古斯塔夫‧拉德布魯赫先生在《法學導論》第一章〈法律和正義〉中寫道:「法律命令的特徵,是某種『定言命令』(der kategorische Imperativ)或誡命,不需要任何內容的說服力,僅僅因為它的存在,便是有效的,我們可以從法律的語言裡清楚地發現這特徵,隨著十八世紀末近代國家的形成,法律的語言也自然而然地出現在法律的精神裡。」因此,法律語言揚棄了勸告(Überredung)的風格、說服(Überzeugung)的風格以及說教(Belehrung)的風格,「當法律因命令性格而褪去了說教或讓大眾理解的成分時,法學就必須取而代之,擔負起法律教導的任務,『成文法保護頭腦清醒的人』(jus vigilantibus scriptum),立法者要預設聽眾是頭腦清楚的,而只有長期和法律打交道,才能獲得這種敏感度。」
只有長期和法律打交道的人,才能對法律語言有敏感度。對法律沒有這種敏感度的外行人聽不懂或看不懂法律語言,當然我們可以說是法律專業人士如律師、檢察官乃至法官等人的說法或解釋還不夠清楚,但因此就說人家「傲慢」和「囂張」,則未免太過。
就拿醫病糾紛來說,當醫師自認解釋得夠清楚或者認為很難花大把時間和功夫去和病患或家屬解釋清楚時,有時往往會被病患一方認為自己並未得到滿意答覆、進而有不被尊重之感,於是許多摩擦與糾紛便因此產生,而這時病患及其家屬就會認為醫生很「傲慢」。這種例子我本人就聽過不少,因為我有親戚本身即是一家私立綜合醫院的院長與主治大夫,我身上所有的動刀手術都是在他們兩兄弟手上完成的。
再來說到我那位台大法律系出身的友人,他不是我「學長」,因為我倆既未曾同校、也不同系,我們的友誼早在大學前就開始了。他長我二歲,和我不僅出生地不同,一個在東、一個在西、中間隔著個中央山脈,連個性、思維也幾乎可說南轅北轍;但關於死刑存廢問題上的支持或反對,卻是我們能不約而同有共識、不致辯到吵起來的少數議題之一。說起來這是三年多前,我倆「一年一會」中、在河堤上看著夕陽、啜飲著咖啡時,所聊到的共有結論。
結論就是:只要冤錯假案疑慮存在一天,我們便不支持死刑的啟動與執行一天。
所以,我們並不反對死刑,就如我那位好友所說的,他反而是「殺人者死」或「殺人償命」這一概念的支持者──對於這一概念我其實有更深一層的省思、這裡就不談了。我們所反對的是,用死刑去處死無辜被冤枉的人。
從你姓潘的舉陳進興的例子來看,顯然你潘某做夢都不會想到,支持廢死的人竟然會不反對處死陳進興這樣的渾蛋吧!三年前我朋友舉的例子正好就是陳進興。
我 們是要為了處死那九十九個有罪的人,而容忍順帶殺了一個無辜者這樣的錯呢?還是為了避免錯殺那個無辜者,而選擇也不殺那九十九個有罪的人呢?
這裡的九十九對一的數字,不過是打個比方,而非什麼學理或調查根據,特此說明一下,也省得姓潘的又頭腦發熱、在這兒「挑骨頭」找茬。
姓潘的說「鄭捷案沒有疑點」,我基本同意,但是不是「鐵案」,還有爭議,因為鄭捷的精神狀況是其中關鍵。如果鄭捷的精神確實是有問題的、而無法對其行為負責,那麼依法便不能對其求處死刑──《中華民國刑法》第19條:「I.心神喪失人之行為,不罰。II.精神耗弱人之行為,得減輕其刑。」不過你姓潘的既然說到鄭捷案,鄭捷說他殺人是為了求得死刑,恰恰就證明了死刑不能遏止這樣的犯罪!這就是你潘某的「盲點」!!
「治亂世用重典」,是我順著前一段的說法附帶提的,死刑是不是「極刑」?極刑能不能稱作「重典」?後面的「法治觀念」也是我自己延伸性的講法,而非出自我朋友之口──你姓潘的沒搞清楚對象便隨便污辱人「放屁」,那麼,「傲慢」的是誰呢?這裡的「法治」是「以法治世」,也就是用法律來管理、防範眾人之犯罪的觀念,和你潘某所說的「沒有人能夠凌駕法律」是兩碼子解釋。怎麼,就你可以講「簡單」定義的「法治」,我就不能說按字面做延伸解釋的「法治」?其次,我有白紙黑字寫「「治亂世用重典」這句話是你說的嗎?套用你姓潘的「邏輯」,我倒要反問你,你「這樣栽贓,不是很卑鄙嗎?」!
還有,我有因為怕「冤案」就說所有的犯罪者都不用為其罪行受到懲罰嗎?有說所有的殺人者都無須付殺人罪的罪刑嗎?如若沒有,你姓潘的指責我「由怕「冤案」要企圖否定一切鐵案」是怎麼來的?再套用你姓潘的「邏輯」反問你一次,你「這樣栽贓,不是很卑鄙嗎?」!!
關於犯罪率與執法效率之間的關係,我朋友那時舉了一非常鮮活的例子。他問我道:假如有事實告訴你,闖紅燈有八成至九成以上機率被逮到並且開罰單時,你會不會很嚴正地考慮要不要闖這個紅燈?我當時毫不思索出口便答:肯定會啊!我在學生時代,摩托車便一直是主要且幾乎唯一的代步工具,時常大街小巷乃至荒郊野嶺到處亂跑,闖的紅燈多了去,我的朋友也是──闖紅燈在台灣可說是屢見不鮮的事、愈往鄉下愈是能見到,所以這個例子對我倆來說,「鮮活」二字那是恰如其分。我朋友還舉了個例子,說明法定得太重有時反而會使得執法者選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或者選擇較輕的罰則開罰;比如說,對違法擺攤的攤販處以罰金,三萬、三千、或者三百,警察開罰的機率便會不同,許多攤販便是迫於生活而不得不出來擺攤,一次開罰三萬、顯然攤販擺上十天半月都不見得賺得了這麼多,警察於是選擇口頭警告、輕輕放過,這很容易理解與體諒,因為法不外乎人情嘛,執法者也是有同情心、惻隱心乃至人情壓力的;反過來說,罰三百,一般人都負擔得起,警察自然也就開罰得不會那麼猶豫。
這段理論和舉例,我相信是我那好友在課堂上聽來的,而非他自己想到的。
以上所述是從人情常理所下的推論與判斷,不過看來潘某人顯然連這點能力都不具備,為啥這麼說?來來來,看看第56期《刑事雙月刊》上的說法(http://www.cib.gov.tw/Upload/Monthly/0142/files/assets/basic-html/page13.html):「傳統上認為,警察查緝、逮捕犯罪人數愈多,愈能嚇阻及預防犯罪……」,結果你潘某人居然說這項論據「很新穎」,不就正好告訴大家你的無知嗎?
沒關係,既然你姓潘的認定非有所謂的「證據」、「學術研究」成果不足以說服別人,你要「證據」、「學術成果」是不是?不要以為我不是法律專業就拿不出來!
可惜許多文本資料現在台灣、我還沒能帶過來,不過就我手邊現有的資源也足夠反駁你潘某。這兩天因為「六四」將近的關係,大陸的互聯網很難連上境外網頁,即使「翻牆」也很不好翻,不過幸好這種資料很容易找,做過這類相關研究的學術論文不在少數,我上網動動指頭一搜,就讓我找著了想引的資料報告,內容就在真理大學副教授兼管理學院院長、管理科學研究所所長莊忠柱以及研究生楊淑芬所撰寫的《影響台灣普通刑事犯罪率因素的探討》論文之中(打上論文標題便能找到):
員警對於犯罪的回應效能,從員警的可見度、反應時間、破案率等方面顯現出來,破案率愈高對犯罪者有嚇阻的作用,因而降低犯罪率的發生。Ehrlich and Brower(1987),利用美國在1946-1977間的資料,指出法律的執行與謀殺、強盜與竊盜罪有顯著的負向關係。Corman , Theodore and Norman(1987)利用美國紐約在1970/1-1984/6間的資料,透過向量自我回歸模型(VAR),發現捕捉率與犯罪率存在顯著的負向關係。Howsen and Jarrell (1987)指出犯罪與都市化的程度有關且破案率與財產犯罪率間存在負向關係。張倉耀、方文碩、林哲彥(1999)研究臺灣在1951-1996年間的年資料,發現破案率與各類型犯罪型(總刑事犯罪率、強盜搶奪犯罪率、賭博犯罪率、煙毒犯罪率與妨害風化犯罪率)均具有負向關係。
即是說,國外與臺灣都有相關的學術報告,並且莊忠柱教授以及楊淑芬的研究結果也與上述報告吻合。
我再附贈網上順手找到的兩篇論文,其一是逢甲大學經濟學系碩士班研究生楊書晴的〈死刑嚇阻效果之探討〉,其「摘要」上明白寫著:
本研究利用1973~2005的年資料,以複廻歸的分析方法,探討犯罪率與嚇阻變數、結構變數、社會變數、經濟變數間的關係,主要發現:
1.警察的破獲率與犯罪率之間存在著顯著的負向關係,即破獲率對犯罪發生率有顯著的嚇阻效果。
2.執行死刑人數比率與暴力犯罪件數發生率有顯著的正關係,但與故意殺人發生率沒有顯著的關係,總體而言,死刑的執行人數比率是沒有嚇阻效果的。
其二是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士研究生黃沄清所寫的〈死刑對重大暴力犯罪嚇阻功能之研究〉,可惜網上無法看到全篇論文內容,不過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士班研究生黃明選所撰之〈我國廢止死刑政策之研究〉論文中可以概窺一二,其云:
本篇論文亦屬量化之實證性研究,旨在研究死刑對重大暴力犯罪之嚇阻功能,並選擇殺人、強盜、強姦、擄人勒贖等四種重大暴力犯罪,及其因此被執行死刑人數為研究母體。經檢驗分析「被執行死刑人數可以嚇阻重大暴力犯罪」,結果沒有證據顯示死刑人數可以嚇阻殺人等四項重大暴力犯罪的發生,也就是說,並無證據足以證明死刑可以嚇阻重大暴力犯罪。這項研究有助解開重典必治世的迷思,所以治亂世用重典是站不住腳的,也說明了重典不符合刑法謙抑思想,死刑之存在絕非必要,這是本篇論文的最大貢獻。
這種互聯網上一查便有的資料,你潘某人憊懶就只想坐著等人給你餵資料,竟也好意思「大刺刺」地「訓話」,預先給結論地說我在「吹牛皮欺騙小孩」?害不害臊啊你!
在羅秉成律師還是臺灣「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執行長時,曾於一次電臺節目中談到:據民調,臺灣有七成八的民眾不相信司法,可是卻有超過八成的人支持死刑;這也就表示,臺灣人一方面不信任司法,卻同時又相信並且支持這樣的司法所判決出來的死刑犯個個都該殺,這難道不矛盾、不荒謬嗎?羅律師又說道:死刑支持者在講述立場時,通常只要持「殺人者死」或「殺人償命」就夠了;可是反對死刑的一方卻往往得要拿出許許多多的理論與實證來努力的說明自己的論點,而這也是臺灣死刑存廢爭議至今仍喋喋不休的重要原因。
接下來,你潘某人要「訴諸權威」是不是?就這麼喜歡被人「壓」??好,我就遂了你的願,搬幾個「權威」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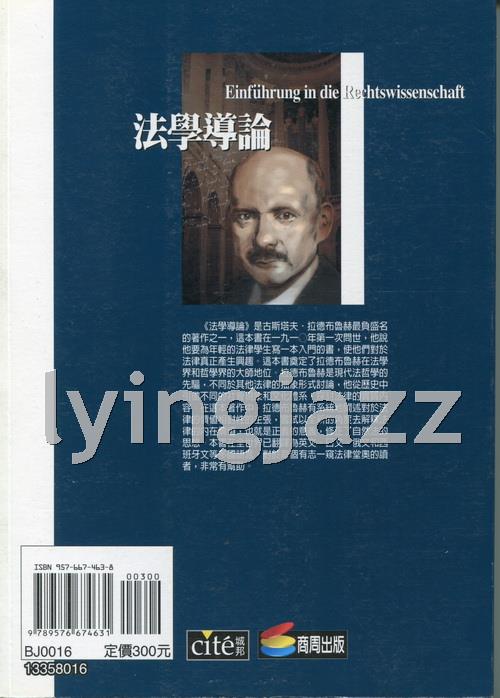 《法學導論》封底掃圖
《法學導論》封底掃圖
這本是古斯塔夫‧拉德布魯赫(von Gustav Radbruch)的《法學導論》──前文中有先引過部分內文,由王怡蘋、林宏濤翻譯,【商業週刊】出版之「人與法律」系列叢書第16號。怕你潘某人不認識拉德布魯赫先生是什麼人,那就抄上一段書中蝴蝶頁上關於作者的簡介吧:「法學界的大師級人物,他是一個法學家、哲學家和社會民主主義者的縮影。在當代的法律思想史上,他已經被公認為一代法學大師,倡導法律相對主義和法實證主義。」
以下是書中第六章關於「刑法」論述的兩段文字:
然而,刑罰的問題已不再只是刑法的建制問題,它還涉及刑法本身的根源。刑罰意味著故意對人施惡,任何人想在這意義下使用刑罰,就必須明確地意識到,他被託付更高層的任務。「人類的力量,若是沒有感受到任何更高的正當化理由,是不足以執行行刑刀。」(俾斯麥在帝國議會之演說,西元一八七○年三月一日)只有以上帝或道德律之名執行刑法,才能心安理得處罰違法者,假若仍只以國家或社會的必要性或目的性執行刑罰,以模糊不清、具有時效性和爭議性的價值觀之名,則執行刑法之手將會顫抖。我們總是有新的大赦,不勝枚舉的特赦、緩刑、減刑,以及形式上規避刑罰等情況發生,這明確地顯示出,刑法已不再能問心無愧。
…………
只要人們仍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血還血!就仍是以報復的方式對待其他人。但今天我們不再說:以眼還眼!不再說:以牙還牙!卻仍然以血還血!只要累犯是搶劫犯和殺人犯,死刑便是根除危險罪犯的方式。現在人類的惡習已經由施暴演進到說謊,這種演進也表現在犯罪上,現在的慣犯不再只是職業搶劫犯和殺人犯,而是以心理學的詭詐從事犯罪的騙徒,和以各種科技的伎倆行竊的小偷。現在的死刑將不再針對原先預期的職業犯,反而經常針對初犯,在他們的一生中,這種惡行可能只是唯一的插曲,死刑已經由對付謀殺犯延伸到其它的範疇,但是沒有任何人希望這樣發展。但死刑的意義不應由案件延用的頻率來衡量,這不表示它在任何刑罰體系中佔居獨一無二的地位。人們根據對刑法的印象,建立對整體法律的判斷,而對於刑法的判斷,則根據最重的刑罰。死刑使刑法令人難以忘懷。因此,死刑使得其它刑罰也顯得殘酷,並且籠罩於凶殘的血腥事件中。在一般觀點下,死刑使刑罰成為用來報復的冷酷刑罰,代表著恐懼和痛苦。在社會教育與保護措施的體系下,不應再有死刑的空間。
羅秉成律師在〈無盡的「蘇案」無盡的奮戰〉一文中寫道(http://www.jrf.org.tw/newjrf/rte/myform_detail.asp?id=3698):
冤錯案件必然存在,理論上或現實上都不存在一套完美無瑕的司法制度,可以擔保冤錯案件不再。冤錯案件本無可畏,可畏的是文過飾非,錯不在我的偏執心態。除了人的問題外,制度也出了問題,才讓沈冤難雪的錯案一再發生。「蘇案」正也突顯出刑事再審制度與非常上訴制度的闕漏不足之處。
現制將許可的門檻拉到高不可攀的程度,形同以制度之手封鎖冤錯案件尋求平反的機會,而且現制要使法院、檢察系統以「自我否定」的方式許可再審或非常上訴,更是難如登天。北歐諸如挪威等國是由獨立於法院、檢察系統之外的機構受理非常救濟案件,以避免自我矛盾的衝突,值得學習。我國如何進一步改造刑事非常救濟制度已是「後蘇案」時期不容迴避的重要立法課題。
覺得羅律師的「冤錯案件必然存在」說法很武斷嗎?那麼我就再引用亞倫‧德蕭維奇(Alan M. Dershowitz)的《德蕭維奇法庭回憶錄》(The Best Deffense,李貞瑩、郭靜美 譯【商業週刊】人與法律16)中〈導論〉裏的一段內容作為旁證:
司法的遊戲規則
在對簿公堂、著書立說以及教學的過程中,我發現美國的司法遊戲實際上似乎有些規則可循,大部分的刑事訴訟的參與者都瞭解它們。雖然這些規則從來沒有被印成文字,可是它們似乎主導了整個過程的真實面。和所有的規則一樣,它們被過分簡化為幾個基本的條文,卻總括了這個體系的實際運作。以下就是司法遊戲運作的幾個鍵性規則:
規則一:事實上,幾乎所有的刑事被告是有罪的。
規則二:所有的辯護律師、檢察官和法官瞭解並且相信規則一。
規則三:違憲比合憲更容易讓有罪被告被定罪,而在一些案件中,不違憲是不可能讓有罪被告被定罪的。
規則四:幾乎所有的警察對於他們是否違憲都說了謊,而這樣做是為了讓有罪被告被定罪。
規則五:所有的法官和辯護律師都知道規則四。
規則六:許多檢察官毫不懷疑地鼓勵警察,對於他們是否違憲一事說謊,而這樣做是為了讓有罪被告被定罪。
規則七:所有的法官都知道規則六。
規則八:大多數進行審判的法官,都會假裝相信明明在說謊的警察人員。
規則九:所有上訴法院的法官都知道規則八,可是有許多法官仍會假裝相信那些假裝相信說謊員警的原審法官。
規則十:大部分的法官並不相信被告對他們的基本人權受到侵害的陳述,即使他們說的是真的。
規則十一:大多數法官和檢察官不會故意將他們相信就其被起訴之罪名(或較輕之罪名)其實是無辜的被告定罪。
規則十二:規則十一不適用於組織犯罪的成員、毒販、常業犯或潛在的線民。
規則十三:沒有人追求正義。

《德蕭維奇法庭回憶錄》封底掃圖
看到了沒有,只要你被警方乃至檢察官認定有罪,即使你真的是無辜的,你仍有非常大的可能被用違憲及撒謊的手段,將你起訴、定罪。而且這還是世界「先進國家」的美國哩!
補充德蕭維奇先生的個人簡介,一樣抄錄自書中蝴蝶頁:「是美國廣為人知的辯護律師,也是著名暢銷書的作者,著有《厚顏無恥》(Chutzpah)、《顛覆命運》(Reversal of Fortune)、《合理的懷疑》(Reasonable Doubt)等作品。他擔任過《耶魯法學論叢》(Yale Law Journal)的主編,1962年自耶魯法學院畢業。二十八歲時即成為哈佛法學院教授,是這所名校有史以來最年輕的教授。1981年,美國刑事辯護律師協會頒獎給他,推崇他『作為學者對於個人自由和人權的卓越貢獻』。」
律師的替人辯護,就和醫師護士的救人一樣,只問自己份內之事、而不問對方是好人壞人還是有錢沒錢,這是最起碼的職業道德。即使是「惡貫滿盈的殺人兇手」也仍要給予最好的辯護,是因為唯有這樣,就算司法對其處以極刑,外界也很難再找到什麼藉口了,因為已給了他最好的辯護──此即是為被告設辯護的初衷與基本精神,這是至少二十年以前我學生時代在圖書館中的一本書裡看來的,別問我書名,因為我早忘了,就算記得,現在恐怕也早絕版了。
所以,我就再掉一次書袋吧,以下兩段文字,引自《丹諾自傳》(The Story of My Life,by Clarence Darrow 簡貞貞 譯【商周出版】人與法律3)中的推薦專文〈期待有更多的丹諾〉:
丹諾發人深省的「犯罪觀」與「辯護觀」,才是人道主義者最可貴的信仰:丹諾認為一個人被宣告有罪,並不等於這個人做了壞事,而只代表這個人看法與一般人不一樣,但這樣的人才更值得去同情、關心與辯護;從這個角度加以引伸,丹諾認為死刑無疑是一種「合法謀殺」,因他堅決替死刑犯辯護,不願做這種「合法謀殺」的幫凶。
……………
在我曾親自經辦的刑案中,不論是財殺、情殺、也不論死者是四個人或警官,更不論是政治動機或單純目的,刑事訴訟「罪疑唯輕」、「與其殺無辜,寧失不經」的證據法則,在台灣的司法有時卻變成「罪疑唯重」,「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人」……,就是這樣造成了不知多少的冤獄。在其中兩件我經辦的重案中,雖然被告一審被判死刑,而在我舉出有利反證後,高等法院改判無罪,但卻在「死刑」加上「無罪」除以二等於「無期徒刑」的台灣司法界「折衷」的判決下,葬送了被告寶貴的青春與司法的尊嚴。
這篇推薦文的作者,我不諱言我很討厭他,但也不會因此便「以人廢言」,他就是臺灣的前總統──陳水扁,這篇專文寫於1999年,那時他還未當上總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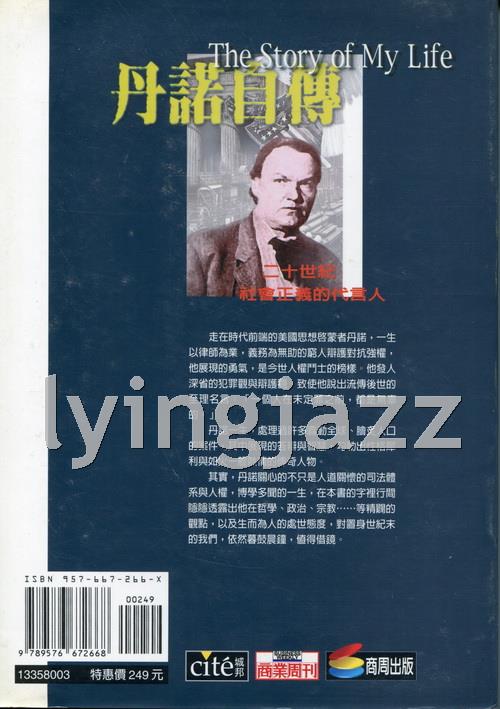 《丹諾自傳》封底掃圖
《丹諾自傳》封底掃圖
手上的這本《丹諾自傳》,購於2000年,是同《法學概論》一起買的,至於《德蕭維奇法庭回憶錄》則購於2002年,我在扉頁上都留有註記及簽章。你潘某人絕想像不到我在法學素養上下了多大的功夫!
最後引《丹諾自傳》第九章中的一段文字作為收尾,其他的懶得和你說了:
說也奇怪,我愈來愈喜歡為被控犯罪的人辯護。這已不再是官司輸贏的問題,我對人類行為背後的成因感到興趣盎然。這不只是和對方律師、陪審團的詭辯,或爭取、保有當事人的錢財以分得我購來或省下來的一分;而是面對著生命──它的希望與恐懼,它的渴望與失望。我認為,處理案件必須深究人類動機、行為和生活調適等根源問,而非盲目漫談仇恨和復仇,以及複雜、含糊的「公義」一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