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家恆(遠流 副總編輯)
卜正民的《維梅爾的帽子》以畫說史,藉著以十七世紀荷蘭畫家維梅爾的幾幅畫(以此為主,但並不以為限),來勾勒十七世紀的全球貿易,這時在歐洲是國家成形並對海外積極擴張的年代,在中國則是明末清初朝代替換的當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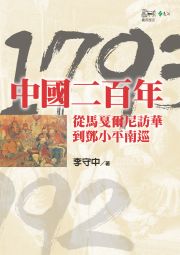 李守中的《中國二百年》則是從康熙開始講,分主題一路講到鄧小平南巡。這個時間取樣明顯含有「以史為鑑」的警示用意。所謂「中國兩百年」,當然就是中國自絕於世界所付出的慘痛代價,而鄧小平南巡所彰顯的意義則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受到挑戰,甚至在北京都施展不開,透過南巡來釋放堅定改革路線的訊息,不容反對人士走封閉的回頭路。
李守中的《中國二百年》則是從康熙開始講,分主題一路講到鄧小平南巡。這個時間取樣明顯含有「以史為鑑」的警示用意。所謂「中國兩百年」,當然就是中國自絕於世界所付出的慘痛代價,而鄧小平南巡所彰顯的意義則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受到挑戰,甚至在北京都施展不開,透過南巡來釋放堅定改革路線的訊息,不容反對人士走封閉的回頭路。
這兩本書有如接力賽跑的選手,時序相接,一個談全球體系建立之初種種事物的關連,一個談的是把大門關上、沒趕上這班列車的後果。這兩棒的交接點則在康熙。
康熙透過耶穌會士接觸到西洋事物,而耶穌會士的策略是利用西洋的科技、知識打入宮廷。基督教早期的歷史對這批來華的傳教士很有鼓舞的作用,在羅馬帝國時期,基督教打入統治階級,甚至讓皇帝也信了教,於是徹底翻轉了基督教的命運,從被迫害的非法宗教,成為帝國的國教(同時也開始迫害其他宗教)。
若是能讓中國皇帝信教,那麼必定能爭取到成千上萬的信徒。在這點上,西方面對中國的態度和夢想始終並無改變。傳教士夢想只要一人信教,基督教就可以讓千百萬條靈魂得救,這就像後來的英國曼徹斯特紡織業者夢想,只要中國人把衣襬放長一點,英國紡織業的生意就做不完,或者到了二十世紀,製造商夢想只要每個中國人買一瓶可樂,業績就會一飛沖天。
在耶穌會當年在華宣教時,用的是「在地化」的策略。當時歐洲文明看待中國文明,是用「仰望」的。來華傳教也是盡量去異求同,就兩個文明的相通點著眼,所以耶穌會士才會在《尚書》裡頭找Deo的翻法,「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將之譯為上帝。
耶穌會這套策略相當奏效,至少給了傳教士無窮的希望。清初傳教士在宮廷中位居要職,作皇帝之師,甚至像湯若望死時,行的是中式葬禮,著清代官服。耶穌會的成就當然讓其他修會道明會相當吃味,往羅馬教廷屢屢告狀,事實上也言之成理,並非純然嫉妒。耶穌會這樣「變通」,到底真正成效如何?「正信」與「異端」的界線在哪裡?
最後,羅馬教皇克萊門斯十四世在一七七三年發佈敕令,停止了耶穌會的傳教活動。這道敕令在歐洲受到不少世俗君王的反對,後來在一八一四年又撤銷。我們可以從一本通俗著作中得到有趣的佐證:大仲馬筆下的《三劍客》,其中一人後來成了耶穌會士,後來王室有難,仍然挺身相救。耶穌會與政治的牽連,由此可見。但是無論如何,一七七三年的命令對於歐洲在中國的傳教活動傷害甚大。
而歐洲看待中國的角度也從「仰望」變成「俯視」,後來來華的傳教活動,沒有早期耶穌會的變通,而是「我不動你動」,中國的信徒若要信教,就得遷就教會,斷無教會遷就信徒的道理。這種態度上的轉變,也就是隱伏在「中國二百年」這麼長的一段下坡路的脈絡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