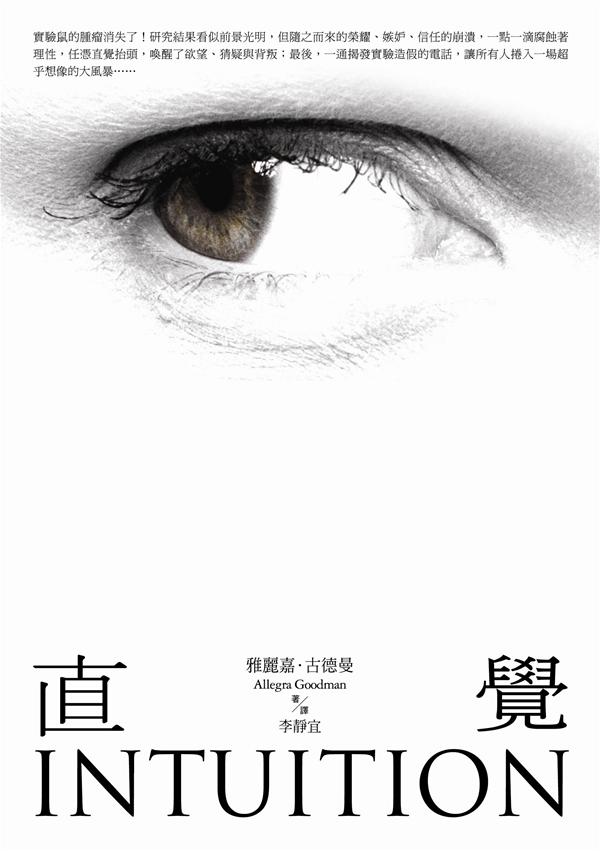 二○○五年底,全世界最大的生物科技醜聞,要數黃禹錫捅出來的漏子。受聘調查的首爾大學李旺載教授形容,事件爆發的十二月十六日是南韓的「國恥日」。黃禹錫先前表示,他曾替十一名病患成功訂製胚胎幹細胞,這項石破天驚的醫療成就,將為帕金森氏症、阿茲海默症與糖尿病帶來革命曙光,論文曾發表於極權威的《科學》期刊。不料調查發現,其中九個幹細胞胚胎根本子虛烏有,唯一成功的兩個也是冷凍胚胎,而非取自病患體細胞培養而成。
二○○五年底,全世界最大的生物科技醜聞,要數黃禹錫捅出來的漏子。受聘調查的首爾大學李旺載教授形容,事件爆發的十二月十六日是南韓的「國恥日」。黃禹錫先前表示,他曾替十一名病患成功訂製胚胎幹細胞,這項石破天驚的醫療成就,將為帕金森氏症、阿茲海默症與糖尿病帶來革命曙光,論文曾發表於極權威的《科學》期刊。不料調查發現,其中九個幹細胞胚胎根本子虛烏有,唯一成功的兩個也是冷凍胚胎,而非取自病患體細胞培養而成。
黃禹錫的騙局早晚會被拆穿,不過還沒推到臨界點就破功。揭發真相的是黃禹錫原本的合作團隊,美國匹茲堡大學的夏騰教授。黃禹錫的手下班底金善顯坦承,他曾經幫黃禹錫把兩個胚胎的照片偽造成十一張。金善顯後來到匹茲堡當交換學者,不得不招出事實真相。醜聞暴發前,黃禹錫主持的「世界幹細胞中心」還曾誘騙首爾大學附設醫院投資二億六千萬台幣,打造全世界最先進的幹細胞臨床試驗基地。
最近台灣書市剛好有兩本以生物科技為背景的小說,可以呼應幹細胞複製醫學的熱況。石黑一雄的《別讓我走》,描寫表面看來是典型英國寄宿學校,其實是供應器官移植的複製人大本營。茱迪‧皮考特的《姊姊的守護者》,則是父母為白血病女兒再生下一個妹妹「備胎」,專門作為供應姊姊輸血、幹細胞乃至腎臟移植的「藥糧」。這兩本小說都有科技與人性的深度觀察,具備預言與寓言的雙重特質。不過如果要反映「黃禹錫事件」,雅麗嘉‧古德曼的《直覺》恐怕更有寫真的趣味。
《別讓我走》與《姊姊的守護者》都有科幻的本質,《直覺》則可說是寫實的浮世繪。這本小說以波士頓的菲爾帕特研究所實驗室為背景,圍繞一樁偽造的動物實驗發展情節。麻省理工的博士高材生克里夫投入兩年半時間,研究呼吸道融合病毒的變異種,希望將裸鼠身上的乳癌細胞轉化成正常細胞。這項結果一旦成功,名利雙收不在話下,諾貝爾醫學獎唾手可得。不過克里夫面臨的卻是大挫敗,不只虛耗兩年半光陰,可能還會被迫離職。
小說一開始就有個詩化的象徵,克里夫走在澄靜、潔白的雪地,宛如一條遭人遺忘的古道。他想出一個大膽的點子,決定徒步越過結冰的查爾斯河面。但踽踽獨行幾步,腳下的冰塊頓時塌沉,河水像冰鉗一樣攫住他,灼痛他的足盤。這個下班的場景,正象徵菲爾帕特研究所實驗室的無菌、淡漠與孤寂,克里夫也在冒一場不會成功的險境。
如果要以導讀者角度就近引譬,讓讀者很快知道作品的風格,我要說,這本小說靠近珍‧奧斯汀甚於麥克‧克萊頓。克萊頓的《奈米獵殺》也是以實驗室工作人員跟家屬為主要角色的小說,他每一部小說都有精彩的科學議題,讓你滿足時下蔚為顯學的頂尖新知。但古德曼並沒有積極解釋呼吸道融合病毒如何變異、如何轉化癌細胞成為正常細胞,克里夫如何作假也不是書寫重點。
珍‧奧斯汀特別在行的,就是封閉社群的人際關係,特別是帶有貧富意識的細描。《直覺》主要角色圍繞在實驗室兩位主管,以及手下幾個博士後研究員,也可以說是一個封閉的長春藤盟校高級知識份子圈圈,這個圈圈隱然也有貧富階級的差別,甚至還有種族因素。古德曼自己是史丹佛的文學博士,不過先生、姊姊都投身波士頓高科技行業,身邊不乏寫作顧問。她以全知觀點描寫動物實驗室種種,仔細而討巧,光這部分就是用功稱職的好小說家。
不過古德曼最拿手的,應是波士頓高科技專才的人際關係網。開宗明義寫克里夫「履冰」之後,小說馬上進入耶誕派對,便是典型「奧斯汀式宴會」。不過,如果每個人都在這個宴會出場,人物介紹恐怕太擁擠,因此范翔這位來自中國的博士後研究員,要在年假之後登場,才得錯落有致的層次感。這本議題新穎的小說,因為作者細膩的布局,而予人十足的古典感覺。作者主要的興趣,不在科技,而在人性。就風格來說,它有珍‧奧斯汀晶瑩剔透的冷眼旁觀趣味,就題旨來說,恐怕更像英國小說家薩克萊的《浮華世界》,刻畫人往高處爬的掙扎與矯飾。
古德曼設計兩場荒誕的情節,達到世俗小說諷刺的本色。其一是《時人》雜誌的專訪,顯示媒體有媒體的生態,不講究實事求是。原本專訪的主角應該是克里夫,但這個按部就班的美國土產博士實在不夠聳動,遠不及來自中國歷經文革洗禮、還沒拿到綠卡的范翔討喜。浮華世界的媒體,雖然不像克里夫那樣直接作假,但他們寧取偏頗的表象,製造事件的譁眾取寵效果,來贏取市場的吸引力。其二是華府的聽證會,控方原本可以藉由這場辯論成功指控克里夫偽造實驗數據,卻因為不小心說出「納粹」字眼,竟然反轉直下變成輸家。科學本應是一翻兩瞪眼的黑白論證,終究不敵法庭語意學的曖昧失言。這本小說在此二處,顯露美式媒體與法庭生態的扭曲面。
我覺得這本小說特別優秀的地方,是它寫出人性的深度,雖然採全知觀點,但不扮演審判長的態度。不過既然主題是作假與背叛,當然有濃厚的道德意味。也許是女小說家的關係,作者對博士後女研究員若冰、實驗室女主管瑪莉安有比較正面的刻畫,我們也不能否定,女性似乎有比較強的道德潔癖與正義感。但對他們愛情或事業的另一半,作者沒有讓克里夫與實驗室男主管山迪變成面目可憎的角色,依然全力描寫他們之所以能出類拔萃的人格特色,使負面角色也有迷人的地方。
此外,這本書沒有侷限在實驗室與法庭,變成廉價的醫學商戰小說,更是其成功處。山迪家的三個女兒與瑪莉安的兒子,雖然對小說主要情節沒有起關鍵作用,但有關兒女教養的描寫,有助全書的理想色彩。從這幾位優秀下一代的思考方式,我們看到美國菁英是如何培育出來的,當然也鑑照出為何有像克里夫這樣甘冒險境而作假的人。舉例來說,山迪是哈佛醫學院入學委員會的主試官,為了說服攻讀科學史的女兒申請醫學院,他說偏離主流的人申請醫學院正風行,像是原本主修英文、音樂家、作家,哈佛醫學院喜歡這類學生。而他自己的實驗室,看中的便是創造力與想像力,像他手下的技術員艾丹,竟可以登台唱《馬太受難曲》的耶穌。這本小說的許多細節,反映美東長春藤盟校高科技白領階級的生活縮影,超過揭發一場學術騙局的層次。(本文作者為作家、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