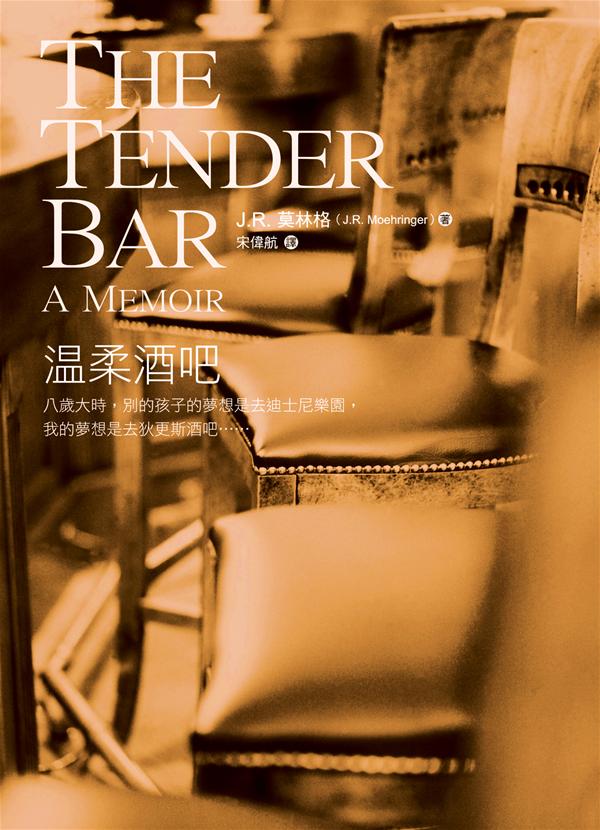
第一部
每個人的體內都有無盡的可能在蟄伏沈睡,絕對不要去作無謂的驚擾。因為,一旦整個人迴盪的都是共鳴回聲,那就會找不到自己真正的聲音了。
──伊里亞斯‧卡內提 《漢普斯戴筆記》(Notes from Hampstead)
第一章 男人家
從小男孩長成酒吧老油條的過程若可以勾畫得很精確的話,那我的就是從一九七二年酷熱的一天夏夜開始。我七歲,在車裏和我母親穿過曼海瑟。我從車窗看出去,看到有九個男的,都穿著橘色的壘球制服,在紀念廣場上四處亂跑。每一個人的胸口都有查爾斯‧狄更斯的側像剪影,黑色的絲網印花。「他們是誰啊?」我問我母親。
「狄更斯他們的人,」她說,「看見你查理舅舅沒有?還有他的老闆史提夫?」
「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她在路邊停下車,我們便到看台找位子。
太陽已經開始西沈,把那幾個人的影子在地上拉得長長的,看起來跟他們胸口的剪影一樣像是絲網印花。還有,那幾個人的鯨魚肚都繫著腰封(cummerbund );鯨魚肚把他們XXL的運動衫撐得往外凸,弄得狄更斯剪影像是那幾個踩在自己影子裏的人潑在胸口的污漬。那幾個人就這樣罩在一層迷離又失真的卡通式趣味裏面。頂上稀疏,鞋子特大,外加上半身膨脹過度,幾個人活像布魯托、卜派,還有吃了類固醇的艾爾摩‧法德(註1);但我高高瘦瘦的查理舅舅除外。他守內野,在內野走來走去像膝蓋痛的火鶴。我還記得史提夫往上揮的那一根棒子是木棒,有電信桿那麼粗,每敲出一記全壘打,球停在空中都像第二個月亮。
史提夫,這一位啤酒大聯盟的貝比‧魯斯(Babe Ruth),站在本壘板上掘地咆哮,怒聲要投手給他一記好球讓他一棒敲得粉碎。投手雖然有一點害怕卻又忍俊不禁,因為,史提夫就算衝著他怒聲咆哮,臉上的笑也從沒停過。他的笑,像燈塔閃現的光,任誰看了都覺得心安。他的笑也像是命令,命令大家跟他一起笑。他那笑啊,無人能擋,不只是他身邊的人;連史提夫自己好像不露出一點牙來實在困難。
史提夫和狄更斯那一幫人拼得很兇,但再怎麼拼,也從來不會擋下他們人生的首要目標──笑。不管比分如何,他們臉上的笑從沒褪過;他們就是沒辦法不笑,看台上的觀眾也是。我就笑得比誰都兇,儘管他們的笑話我聽不懂。我在笑他們的笑,我在笑他們搞笑的時間點抓得真準,流暢,靈活,一如他們的轉身雙殺。
「他們怎麼這麼寶啊?」我問我母親。
「因為他們──開心啊。」
「什麼事開心?」
我母親看著他們想了一下。
「啤酒,小乖。他們開心有啤酒喝。」
每一次那些人跑過去,都會留下一團氣味。啤酒。鬍後水。皮革。菸草。護髮露。我深吸一口氣,把他們的味道記在心裏,把他們的精髓記在心裏。從那一刻起,我每一聞到一桶「謝佛」,一瓶「費華」,剛上過油的「斯伯丁」棒球手套,閃著火星的「福運」,長頸瓶的「菲達力」(註2),就會回到那一刻;那一刻,有我母親在身邊陪著,看那幾個虎背熊腰的啤酒幫在鑽石形的框框裏又跌又撞。
那一場壘球賽於我是許多事的起點,尤其是時間的起點。我在那一場壘球賽之前的記憶,都是片斷的,零碎的;之後,記憶就以一字縱隊整整整齊齊的大步前行。可能是我必須先找到那一家酒吧吧;那酒吧是我人生的兩大組織原則裏的一條;有了這,我才有辦法將人生作線性、連貫的敘述。我記得那時我還跑去找我人生的另一大組織原則,跟她說我要一直看他們打球不走。不行,孩子,她說,球賽已經結束。啊?我愣在那裏,好不驚慌。那一幫人是在朝場外走去,幾個人勾肩搭背一起離開。他們的人影沒入紀念廣場周圍的漆樹叢裏,再傳來他們的吆喝,「狄更斯再見啦!」我哭了起來,急著要跟上去。
「為什麼?」我母親問我。
「去看什麼事那麼好玩。」
「我們不可以去酒吧,」我母親說,「我們要回──家。」
她每一次講到這個字都不順。
我母親帶著我住在我外公家裏,他那房子也算是曼海瑟的地標,跟史提夫的酒吧幾乎要齊名了。常有人從外公的房子前面開車過去,指指點點的;我有一次還聽到有從外公房子外面走過的人在猜,外公這房子準是得了「痛苦的屋癌」。這房子得的是什麼病,要看拿什麼來比。若是放在曼海瑟雅致的維多利亞薑餅屋(註3)和雄偉的荷蘭殖民地(Dutch Colonial)風格中間,那外公要倒不倒的鱈魚角(Cape Cod)式房子就加倍恐怖。外公的說法是他修不起房子,但其實是他才不在乎。他還橫眉冷眼,乖張又自負的說自己的房子是「狗屎屋」;連屋頂已經開始往下凹,活像是馬戲團的帳篷,他也不以為意。牆面的油漆一塊塊剝落,都有撲克牌那麼大,他照樣視而不見。外婆指著車道歪歪扭扭的裂縫給他看,他就當著外婆的面給她一個大呵欠,像當它是天上的閃電打的──還真的是天上的閃電打的沒錯。我那幾個表姊是真的看到有閃電嘶嘶打中車道,差一點就要打中風廊了。那時,我想連上帝都在朝外公的房子比手指頭呢。
我母親就帶著我,和我外公、外婆、我媽的兩個同胞手足──查理舅舅和露絲阿姨──還有露絲阿姨的五個女兒、一個兒子──同住在這一戶往下塌的屋頂下面。「一夥兒全擠到這裏來搶沒房租的自由。」這是外公形容我們的說法。史提夫在普蘭登路五百五十號建立起他的公共殿堂;外公則是在普蘭登路六百四十六號管理一家破落「公」寓。
外公若在他的大門上面也釘一幅狄更斯的側像剪影,未嘗不可;因為,他那房子的景況直追狄更斯筆下的囚犯工廠。只有一間浴室可用,但有十二個人。「等」,在外公家可常是一大折磨。化糞池也老是滿溢(「狗屎屋」有的時候可不只是尖刻的諢名而已。)每天早上,要洗到二號才有熱水出來;洗到三號時,略給你一段「小品」嚐嚐;之後,就開始戲弄你,到後來,乾脆橫下心腸硬是對四號不理不睬。家具有很多的年代,可以上溯到小羅斯福總統的第三任時期,纏過一層大力膠(duct tape)帶再纏過一層大力膠,才沒有散掉。家裏算是新的東西,就只有喝水用的玻璃杯;還是從狄更斯「借來」的。另外,跟施樂百百貨(Sears)買的客廳沙發,布套印的花樣是自由鐘加禿鷹加幾個美國建國元勳,醜到可以把你催眠。我們叫那沙發「兩百年紀念沙發」。雖然喊得早了幾年,但外公說這名字取得正好,因為,那沙發的樣子正像被喬治‧華盛頓當年拿去用來橫渡德拉瓦河(the Delaware)。
住在外公家裏的日子,最慘的就是吵,二十四小時吵鬧不休,有罵,有哭,有吵架,有查理舅舅大吼他要睡覺,有露絲阿姨厲聲罵她的六個孩子;刺耳的叫罵像海鷗的嘎聲長鳴,把你的神經撕成片片。而在浮盪的喧鬧下面,壓著節奏穩定的震動,一開始不明顯,等你注意到了,就變得比較大聲,像厄榭老屋(註3)地底的心跳。但「外公老屋」的心跳是紗門整天人進人出、開開關關──刷──砰!刷──砰!──加上我家裏的人一個個走路都有特色:重心放在腳跟上面,踩得很重,像突擊隊踩高蹺。就在叫罵加紗門加吵架加重重的腳步聲之餘,等到了日薄西山的時候,屋裏的吆喝、震動,連狗都退避三舍,一有機會就馬上開溜。但傍晚是漸強的高潮,是一整天人聲和衝突達於鼎沸的時刻;因為,傍晚是晚餐的時刻。
我們大家在朝一邊歪的晚餐桌邊團團坐好後,一夥兒人馬上一起開動:講話;這樣就不必專心吃東西。外婆不會作菜,外公不肯多給她一點錢作家用;所以,裝在有裂口的大碗從廚房裏端出來的,會吃死人也笑死人。外婆說的「肉丸義大利麵」,作法就是把一整盒義大利麵扔進鍋煮到糊成一團,再倒一罐康寶(Campbell)番茄濃湯進去攪拌均勻,再在最上面擺上幾條生的熱狗,就大功告成。鹽和胡椒,自行酌量添加。但真讓人消化不良的,還是外公大人。他那人獨來獨往,不與人交,彆扭難纏,還有口吃;這樣的性子,卻落得每天晚上一坐上餐桌主位,就要面對十二個不速之客──連狗也算進去的話。真像是愛爾蘭破落戶演出的「最後的晚餐」。他那一雙眼睛盯著我們來來回回看的時候,我好像都聽得到他在心裏面嗯哼,你們中間每一個與我同桌的人今天晚上會出賣我。(註5)但是,外公從沒表示過不歡迎誰,這一點是要謝謝他。只是,他也從沒讓人覺得他歡迎過誰。他還時常喃喃叨唸,說我們一個個「全都該給我掃地出門才對」。
我和我母親走得成的話,當然樂意馬上走人,只是,我們沒地方可去。她賺的錢很少,從我爸爸那裏也拿不到一毛錢。我爸爸不想和他妻子還有他唯一的骨肉有一點瓜葛。我爸爸那人是個頭痛人物,獨具的魅力加火爆的脾氣很不穩定;我母親別無選擇,只有離開一途;那時我只有七個月大。而我父親的報復就是不告而別,外加斷絕一切援助。
由於他鬧失蹤的時候我還太小,因此,我連他長個什麼樣子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講話的聲音,而且熟悉得很。我爸爸是很紅的搖滾樂DJ,每天都在紐約不知哪裏對著大大的麥克風講話,隨他渾厚的男中音飄過赫德遜河(Hudson River),沿著曼海瑟灣穿梭過來,在普蘭登路上聚焦,一毫秒後,就從我外公放在廚房桌上的那一具橄欖綠的收音機裏,播放出來。我爸爸的嗓音很低沈,聽起來很兇險,聽得我胸廓轟轟震動,廚房裏的器皿咔咔輕顫。
外公家裏的大人都很保護我,假裝根本沒我爸爸這個人存在。(我外婆甚至連他的名字都不肯提起──我爸爸叫作強尼‧麥可茲﹝Johnny Michaels﹞──若不提他不行時就叫他「那聲音」。)他們一聽到我爸爸的聲音,會馬上跳起來伸手換頻道,有時,連收音機都藏起來,氣得我嚎啕大哭。由於我身邊繞的都是女的,另兩個男的也和我不親近,因此,「那聲音」在我就成了我和男性世界唯一的聯繫。此外,「那聲音」也是我要蓋掉外公家那些討厭聲音的唯一門路。「那聲音」,每一天晚上都在橄欖綠的盒子裏開派對,不是當史提夫‧汪達就是范‧莫里森(註6),要不就是披頭四(the Beatles),是我用來對抗身邊一切喧鬧的仙丹。外公、外婆為了家用的錢吵架的時候,露絲阿姨氣得拿東西摔牆的時候,我只要把耳朵貼在收音機上,「那聲音」就會跟我說有趣的事,或放一首「薄荷彩虹」(註7)的歌給我聽。我聽「那聲音」聽得之入迷,別的聲音全都會被我關在外面;我這本領之高強啊,讓我小小年紀就成了「偏聽」神童。這在我以前以為是我的福氣,但後來卻發現卻是災阨。人的一生,就一直在挑你要聽的聲音,在挑你不想聽的聲音;這一堂課,我比大部份的人都要早學到,但也比大部份的人要晚才學會應用得當。
我還記得有一天晚上我轉到我爸爸的頻道時,覺得特別孤單。因為,我爸爸那一天播的第一首歌是「四季合唱團」唱的〈回到你身邊〉(註8),之後,他再用他最溫柔、最甜膩的腔調,聽得你像是看得到他臉上的笑,說,「我就要回家了,媽啊──但耐心一點,我只有一張送報路線圖。」我閉上眼睛,笑了,一時間忘了自己是誰,人又是在哪裏。
--------------------------------------
註1:布魯托(Bluto)、卜派(Popeye),艾爾摩‧法德(Elmer Fudd),都是卡通裏的角色。卜派就是大力水手,布魯托是專門找他麻煩的那一個壯漢,艾爾摩‧法德是滿嘴嘰哩咕嚕、拿著獵槍要對付兔寶寶的那一個矮個子。
註2:「謝佛」(Schaffer)──正確的品名應作Schaefer,美國老牌啤酒廠;常見誤作Schaeffer。
「費華」(Aqua Vellva)──美國老牌男士保養品牌。
「斯伯丁」(Spalding)──美國運動品牌。
「福運」(Lucky Strike)──美國老牌香菸,中文也作「好彩」。
「菲達力」(Vitalis)──美國男性護髮品牌。
註3:維多利亞薑餅屋(Gingerbread Victorian)──gingerbread(薑餅)用在形容建築,指過於縟麗、華美的風格。
註4:厄榭老屋(House of Usher)──偵探小說鼻祖愛倫‧坡(Edgar Allen Poe;1809─1894)一八三九年出版過一篇恐怖小說〈厄榭老屋傾頹記〉(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
註5:你們中間每一個與我同吃的人今天晚要賣了我──依《新約聖經》記載,耶穌在最後的晚餐上曾經對同桌的十二個門徒明指有一人背叛了他。此句譯文乃以中文聖經和合本為本略作改寫。
註6:史提夫‧汪達(Steve Wonder;1950─)──美國著名的黑人盲樂手,從一九六O年代才十幾歲時就紅遍全球,金曲無數。范‧莫里森(Van Morrison;1945─)──北愛爾蘭籍的搖滾樂手,一九六O年代開始走紅。
註7:「薄荷彩虹」(Peppermint Rainbow)──走紅於一九六O年代末期的美國女子輕搖滾樂團。
註8:「四季合唱團」(Four Seasons)──走紅於一九六O年代的美國義大利美聲樂團,〈回到你身邊〉(working My Way Back to You)是該團一九六六年的金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