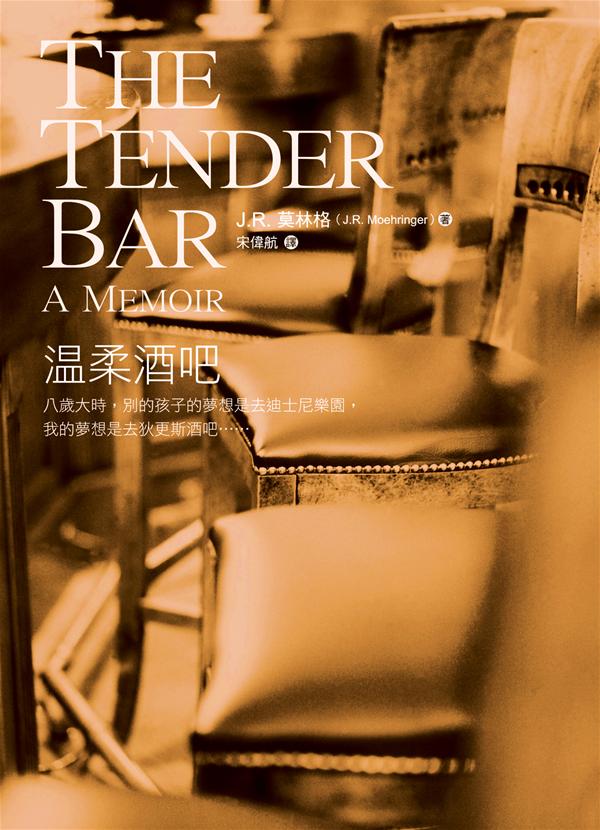 我們一有需要就到那裡去。渴了當然去。餓了去。累得要死也去。高興的時候去,去慶祝。難過的時候去,去生悶氣。婚禮過後去。葬禮過後去,去找東西安定心神。之前,更一定要去,去打強心針。不知道自己要什麼的時候一樣去,去看是不是有人說得出來我們要什麼。尋找愛,需要性,想找碴,一概都到那裡去。要不就是協尋失踪人口;因為,大夥兒遲早都會打從那裡冒出來。還有,我們想讓自己被人找到的時候更一定要去。
我們一有需要就到那裡去。渴了當然去。餓了去。累得要死也去。高興的時候去,去慶祝。難過的時候去,去生悶氣。婚禮過後去。葬禮過後去,去找東西安定心神。之前,更一定要去,去打強心針。不知道自己要什麼的時候一樣去,去看是不是有人說得出來我們要什麼。尋找愛,需要性,想找碴,一概都到那裡去。要不就是協尋失踪人口;因為,大夥兒遲早都會打從那裡冒出來。還有,我們想讓自己被人找到的時候更一定要去。
我自己的需求表有一大串。我沒有兄弟姊妹,我爸爸還不要我;我需要親人;我需要家;我需要男性。還以男性最重要。我需要男性來當我的精神導師,來當我的偶像,來當我的角色模範,來當我陽剛的砝碼,好和我母親、我外婆、我五位表姊妹抗衡;我和她們住在一起。我需要各色各類的男性,這些酒吧裡都有。而我最最不需要的那一、兩位,酒吧裡也有。
早在酒吧依法可以讓我進去之前,酒吧就已經是我的救星。孩提時代重建我的信心,少年時代照料我的需求,青年時代包容我的一切。雖然我一直怕我們忍不住要靠過去的,往往就是最不想要我們的,最有可能拋棄我們的。但到頭來,我卻相信我們之為我們,就是由包容我們的一切在界定的。我自然也以包容這一切作回報;直到有一天晚上,酒吧不讓我進去了。終遭見棄,卻救了我。
但凡是街角就會有酒吧,不管是叫酒吧或是叫什麼;打從開天闢地起,或說是打從禁酒令撤銷起吧,就是這樣。開天闢地跟撤銷禁酒令在我住的這一處嗜酒小鎮是同一件事──我住在長島曼海瑟(Manhasset,Long Island)。一九三○年代,酒吧是電影明星要到附近的遊艇俱樂部或豪華濱海度假別墅去時的中途站。一九四○年代,酒吧是戰後士兵返鄉的避風港。一九五○年代,酒吧是飛機頭小子挽著捲毛獅子狗裙的女友閒晃的安樂窩。不過,酒吧變成地標,變成一塊有光環的聖地,則要再等到一九七○年。那一年史提夫買下了那地方,改名作「狄更斯」(Dickens)。史提夫在門上掛了一幅查爾斯‧狄更斯的側像剪影,還在剪影下用古英文字體寫上:(※※影印圖,原書p.4)。史提夫大辣辣將他的戀英情結公告周知,頗教曼海瑟的凱文‧弗林和麥可‧蓋勒格[1]者流如坐針氈。但他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純粹是因為他們對史提夫立下的天字第一號酒吧內規心悅誠服:第三杯免費。不止,還有別的事也不無小補;史提夫雇了七個還是八個歐麥利幫的人來替他跑堂,還費了一點心思,把狄更斯弄得像是從竇納加爾一磚一瓦運過來的。
史提夫要他的酒吧看起來有歐洲小酒館(public house)的氣質,但感覺起來要有純正的美國風味,是如假包換的公眾場所;他的公眾。曼海瑟在曼哈頓東南方十七英哩開外的地方,是人口八千、田園風的郊區。史提夫要在曼海瑟的中心蓋一座庇護眾生的聖殿,供他的鄰居、朋友、酒伴,尤其是他越戰歸來的高中死黨,能嚐到一絲平安的滋味,而後再度光臨。史提夫每次創業無不信心飽滿──信心是他最大的魅力,卻也是他的致命傷──但狄更斯超過了他最大的想望。曼海瑟這地方未幾就把史提夫的酒吧奉作世上絕無僅有的一家酒吧。我們不都是拿「城裡」(The City)指「紐約市」,拿「街上」(The Street)指「華爾街」的嗎?所以我們裡一說「酒吧」,十之八九,絕不會有人搞錯這是在說哪一家酒吧。後來,狄更斯又不知不覺變得不只是「酒吧」。狄更斯變成「那裡」,成為能為生命遮擋一切風雨的庇護所。一九七九年三哩島(Three Mile Island)核電廠發生災變,末日降臨的驚懼橫掃東北角,曼海瑟的居民紛紛打電話給史提夫,要他在他酒吧下面密不透風的地下室裡替他們留空位。大家當然都有自家的地下室。只是,狄更斯不一樣。正當浩劫陰森在目,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狄更斯。
除了庇護之外,史提夫也在他的地方提供夜間部民主課程,或者是酒精提煉的特殊多數決。只要往他的酒吧中間一站,準會看到男男女女,各色人等一個個忙著在教育別人、忙著在教訓別人。鎮上最窮的人,可以跟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所長討論市場波動;鎮上圖書館的館長,可以在紐約洋基隊的名人堂球星面前,大談球棒要抓在中段的道理。頭腦不清的門房發表高見,荒誕不經卻是真知灼見,一樣聽得大學的哲學教授忙不迭拿紙巾寫下,塞進口袋收好。至於酒保呢──在忙著下注、調粉紅松鼠(Pink Squirrel)之餘──也是一開口就有哲學家國王的架式。
史提夫相信在全美國的聚會場所裡,人人平等的理想要能發揮得最淋漓盡致,就屬街角的酒吧;他也知道酒吧、沙龍、旅店(tavern)、「酒舖子」(gin mill)等等地方,在美國人的心裡始終據有一席崇隆的地位──「酒舖子」還是他最愛的說法。他深知美國人為他們的酒吧加上了一層意涵;凡有所求,就往酒吧裡去,不管是求魅力還是助力都好;想要掙脫現代生活的凌遲──寂寞,更是要去。但他有所不知:當年清教徒一落腳新大陸,還沒蓋教堂就先蓋起了酒吧。他另也有所不知:美國人的酒吧是《坎特伯里故事集》裡面喬叟寫的中世紀酒吧的嫡系後代;喬叟的酒吧則是薩克遜麥酒舖的嫡系後代;薩克遜的麥酒舖又是古羅馬時代路邊塔缽的嫡系後代。史提夫開的酒吧追本溯源,可以上達西歐的洞窟壁畫;石器時代的部族長老就是在洞窟裡面為少男、少女上課,教導部族裡的規矩;那時間是近一萬五千年前的事了。雖然史提夫不知道這些,但這些就在他的血脈裡面,他感覺到了,而且發揮在他做的每一件事上面。史提夫比大部份的人都更能體會場景有多重要,也以這為基石,創立了這麼一家酒吧,古靈精怪的,備受愛戴,和顧客聲氣相通,令人歎服,名聲遠播到曼海瑟之外。
我的家鄉小鎮以兩件事出名──長曲棍球和酒。年復一年,曼海瑟身手過人的長曲棍球手新人輩出,數量特多;至於腫大的肝,數量就還要更多。另有一些人也知道曼海瑟是《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故事背景的所在。費茲傑羅這一部傑作有一部份,就是坐在大內克(Great Neck)微風徐徐的陽台上面寫就的。他的眼光一越過曼海瑟灣(Manhasset Bay)就會看到我們這座小鎮。他就把我們的小鎮變成他小說裡的東艾格(East Egg)。這是歷史性的殊榮,我們的保齡球館和披薩店因之蒙上了考古的光環。我們每天都走在費茲傑羅廢棄的舞台佈景裡面。我們在他的廢墟裡相互投射浪漫的色彩。這是這裡的話題──這是這裡的榮耀。但是,這也跟史提夫的酒吧一樣,都是曼海瑟出名愛酒而衍生出來的枝節。熟悉曼海瑟的人都會知道,為什麼酒在費茲傑羅的小說裡會跟密西西比河流過泛濫平原一般泛濫成災。怎麼那些男男女女會不停的辦喧鬧的派對,不停大灌黃湯,不到喝掛了或開車撞死人不曉得要停?這在我們聽起來,就很像曼海瑟典型的星期二之夜。
曼海瑟有紐約州最大的酒類專賣店,也是長島唯一名稱掛在雞尾酒上的小鎮(「曼海瑟雞尾酒」就是「曼哈頓」,只是酒精更重)。曼海瑟鎮上半哩長的大街,普蘭登路(Plandome Road),是全天下酒鬼的夢想大街──一家酒吧連著一家酒吧再連著一家酒吧。曼海瑟有許多人把普蘭登路比作愛爾蘭神話裡的鄉間小路,上面有蜿蜒的人龍,男男女女滿肚子威士忌和好心情。普蘭登路上的酒吧多如好萊塢星光大道的雲集眾星。而我們對酒吧林立的盛況,也有頑固而古怪的自豪。有個人曾經為了保險金而燒掉了他開在普蘭登路上的酒吧。警方在普蘭登路上的另一家酒吧裡面找到他,跟他說有事情要問他。那人舉起一隻手搭在胸口,像神父被控燒了十字架,說,「怎麼會?」他反問道,「怎麼會有人──做得出來燒掉酒吧這樣的事?」
這裡的組成很是古怪,分成上流階級和勞工階級兩邊,族裔是愛爾蘭加義大利,還有全美頂尖富豪家族的小圈圈湊上一腳,弄得曼海瑟始終在為自己的定位掙扎。這一座小鎮有一臉髒兮兮的頑童在紀念廣場(Memorial Field)上流連──玩他們的「單車馬球」;有鄰居躲在自家整整齊齊的樹籬後面老死不相往來──卻對彼此的事蹟、弱點如數家珍;而且,人人天剛破曉就搭列車上曼哈頓去──卻也沒人真的一去不返;裝在松木匣子裡除外。不過,曼海瑟感覺起來還是比較像小農村;雖然有房地產仲介愛叫這裡「臥室社區」,我們自己倒是死守著「酒吧社區」的名號不想放。酒吧給了我們身份,酒吧給了我們交集點。少棒,壘球,保齡球,初級聯賽,不只都在史提夫的酒吧裡開會,往往還挑同一晚開會。
「黃銅小馬」(Brass Pony),「歡樂殿」(Gay Dome),「檯燈(Lamplight),「基爾米德」(kilmeade's ),「瓊恩艾德」(Joan and Ed's ),「啪!」(Popping Cork),「一六八○」(1680 House),「二輪馬車」(Jaunting Car),「抓癢癢」(The Scratch)──我們對曼海瑟的酒吧,比對曼海瑟的街名還有創鎮世家都還要清楚。酒吧的壽命很像朝代:我們都用酒吧的壽命來記時間;而發現曼海瑟每關一家酒吧馬上就會另開一家,打心底裡快慰不少。我外婆跟我說過,曼海瑟這地方是把「老太婆的碎嘴子」當作傳家寶訓來看的──她這說的是:躲在家裡喝酒是酒鬼的徵兆。也因此,只要公然喝酒,沒在私底下偷偷喝,就不算酒鬼。所以,酒吧!好多家、好多家酒吧!
曼海瑟的酒吧有許多當然都跟別的地方一樣,都不算是高雅的場所,一堆爛醉如泥的人泡在悔不當初的呢喃自語裡面臭不可聞。史提夫就要他的地方與眾不同。他要他的酒吧鶴立雞群。他構想的酒吧,要有包容曼海瑟各色人等的肚量。他的酒吧可以前一分鐘是安逸的公共小酒館(pub),後一分鐘就變成了下班後的狂歡夜店(club)。傍晚時是家庭式餐廳,夜深後就變成低俗的小酒店,隨店裡的男男女女大吹牛皮、爛醉到掛都可以。史提夫構想的核心,就是狄更斯必須是外在世界的反面。酷熱時沁人心脾,初次霜降後就要溫暖如春,直到春來。他的酒吧始終都很乾淨,光線明亮;像最美滿的家裡面的書房,我們全都相信會有,但現在不存在、以前也沒有過的美滿的家。每個人到了狄更斯,都會覺得自己與眾不同,但又不會成為眾矢之的。史提夫酒吧裡流傳的故事,我最喜歡的可能就是:有一天,有人從附近的精神病院跑了出來,摸進了史提夫的酒吧。沒人多瞄他一眼。沒人問他是誰,沒人問他為什麼穿的是睡衣,沒人問他為什麼眼露凶光。大夥兒在酒吧裡照樣和他勾肩搭背,講笑話給他聽,買酒請他喝,鬧上一整天。只是,這可憐蟲最後還是被請了出去,緣故是:他的褲子忽然掉下來,原因不明。但就算這樣,酒保也只是輕輕罵他一句,用的是酒吧裡的標準告誡:「唉呀老兄──不可以這樣子啦。」
酒吧像愛情,靠的是時機、靈犀、火花、運氣,還有──這可能才是最重要的──寬容。史提夫從一開始就聲明,到狄更斯來的人沒一個會被看輕。他店裡的漢堡一定是三吋厚的舒芙蕾(soufflés)腓力牛排肉。他關門的時間都可以商量──管它法令怎麼規定。他的酒保都會多倒一點──不止一點。狄更斯一杯的標準份量,在別的酒吧一定看作是雙份。而狄更斯的雙份,準教你喝成鬥雞眼。至於三份嘛,你就會「菠菜加奶油」了。這是我舅舅查理的獨創說法。他也是史提夫請的第一個酒保。
史提夫是道地的曼海瑟子弟,信奉黃湯。他的一切,他全歸諸黃湯所賜。他父親以前是海尼根的經銷商,死時留給史提夫一點財產;史提夫那時還很年輕。史提夫叫女兒白蘭蒂(地);叫他的快艇「醉仙」(dipsomania);他那一張臉經過多年荷馬式狂飲[8],一片緋紅,就道盡了一切。他自比作「酒徒的斑衣吹笛人」,而曼海瑟醉眼惺忪的居民也這樣子看他。多年來,他就這樣召來了一大批人狂熱追隨,像是一批信徒軍團。「史提夫崇拜」是謂。
世人都有其聖殿,有其避難的處所;人到了那裡,心靈就會比較純潔,心智就會比較清明,他的上帝、或愛、或真理、或管他信奉的是什麼,感覺上也變得比較親近。好壞不論,我的聖殿正好就是史提夫的酒吧。而且,由於發現這寶地時我年紀還小,因此,他的酒吧於我就更顯得神聖多了,始終罩在一層特殊的莊嚴裡面;小孩子對他覺得安全的地方,都會覺得莊嚴。別人可能是對教室、操場、戲院或教堂、實驗室、圖書館、體育館有這樣的感覺吧。甚至家。但這些地方都與我無緣。我們禮讚的都是近在咫尺的對象。我若是在河邊或海邊長大,而且有大自然讓我可以發覺自我或躲得進去,那我崇奉的很可能就是大自然。但我不是。我是在一家出類拔萃的美國酒吧往旁再走一百四十二步就到了的地方長大的;就此天差地別。
我倒不是只要醒著就在酒吧裡混。我一樣投身世界;工作過;失敗過;談過戀愛;當過蠢蛋;也心碎過;韌性的門檻在在遇過考驗。但就由於有史提夫的酒吧,每一次的過渡儀式,感覺都和前一次連在一起,也和後一次連在一起;我遇過的每一個人也是。打我出生後的前二十五年,我認識的人,不是叫我到酒吧,就是開車送我到酒吧,不是陪我到酒吧,就是把我從酒吧裡扛出來,或是在酒吧裡等我,而且,好像打從我一出生起就在那裡等著我了。史提夫和他酒吧裡的那一夥人,就屬於後面那一類。
我以前常說我是在史提夫的酒吧裡面找到我需要的父親的,而且是好多個父親;但也未必盡然。有時候,酒吧就是我的父親;他那酒吧裡的好幾十個人,融合成一個奇大無比的男性之眼,照看著我,提供我母親沒辦法給的另一半,她的X染色體之外的Y染色體。我母親不知道她必須和酒吧裡的那一幫男人競爭;酒吧裡的那一幫男人也不知道他們在和她比賽。他們全都以為他們一個個都是一樣的;因為,他們對「男人家」的看法全都很老派。我母親和那一夥兒人都認為當好男人是一門藝術,當壞男人是一件慘事;這不僅是對依賴這個不幸男人的人講的,全世界都一樣。雖然這觀念我最早是從我母親那裡得來的,但其間的道理,則要在史提夫的酒吧裡日日看它驗證。史提夫的酒吧一樣有許多女子慕名而來,形色之多,目不暇給。只是,我的注意力全在他酒吧裡各色各類的好男人、壞男人身上。我就悠遊在這一群天下少有的老大兄弟會裡面,聽大兵、球員、詩人、警察、富豪、組頭、演員、騙子講他們的事;他們夜夜都歪在史提夫的吧台上,我就聽他們一遍說過一遍,聽他們說他們之間的差別有多大,只是,他們差別這麼大的理由卻不大。
一堂課,一個動作,一則故事,一樣哲理,一種態度──我從史提夫酒吧裡的每一個男人身上一概要得到東西。我在「盜用身份」這件罪行還沒搞得那麼惡劣的那年頭,就已經是「盜用身份」的高手了。我學會跟藍球高手(Cager)一樣凡事冷嘲熱諷,跟查理舅舅一樣凡事嬉笑怒罵,學會跟喬伊迪(Joey D.)一樣凡事蠻橫無理。我想跟條子鮑(Bob the Cop)一樣實在,跟小馬(Colt)一樣酷;滿肚子火時就拿臭頭(Smelly)來給自己作理由,說我哪比得上他的正義怒火。到後來,我拿我在狄更斯學到的模仿工夫用在我在酒吧外面認識的人身上──朋友,情人,父母,老闆,甚至陌生人。酒吧在我身上養成了一種習慣,讓我在人生道路不管遇上了誰,一概把人家變成我的良師益友,或是劇本裡的角色。這都要歸功史提夫的酒吧,也全要怪史提夫的酒吧,害我變成天下人的反映,或說是折射。
史提夫酒吧的老主顧一個個都愛用比喻。有一個專喝波本威士忌的老人家就跟我說,男人的一生就像山和谷──山是我們要去爬的,谷是我們沒辦法面對山的時候可以躲的。酒吧於我而言,既是山,也是谷。是我最豪華的谷地,也是我最危險的山巔。而裡面的人,雖然在心底是山頂洞人,但一個個都是我的雪巴。我愛他們,打從心底愛他們,我想他們也都知道。雖然他們什麼事沒遇見過──戰爭,愛情,盛名,恥辱,財富,破敗──但我想,他們也從沒遇過小男孩睜著那麼一雙晶亮、崇拜的眼睛仰望他們。我的崇敬是他們從沒有過的經驗,我想他們因此也算是愛我的吧;用他們的方式愛我。所以,他們才會在我十一歲的時候把我綁走。但現在,我好像聽得到他們在說:哇!小子欸,你都要趕上我們了。
至於史提夫,倒可能要我這樣子說:我愛上了他的酒吧,而且,還不是單向道的愛。而且,我其他的愛,全都是從我和他酒吧的愛所衍生來的。我還在青澀的年歲便有幸站在狄更斯裡面;那時我就知道,人生就是一連串的愛戀,每一場新的愛戀,都是前一場愛戀的回應。但在史提夫的酒吧裡悟出這番道理的人,絕不只我一個浪漫派而已,而是有很多個浪漫派,一個個全都相信愛有這般的連鎖反應。就是有這般的信念,當然還有這樣的酒吧,才把我們都綁在一起。也因此,我說的故事,只是一大股線裡的一綹,這一大股線,把我們的愛戀故事全都編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