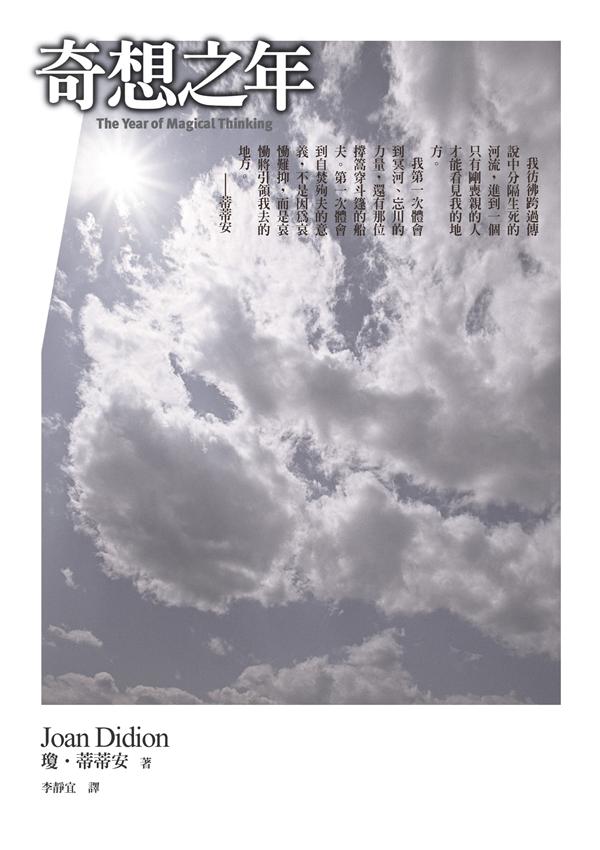
我也知道,如果我們想自己繼續過下去,到了某個時間,我們就必須對逝者鬆開手,讓她們走,讓她們死去。讓他們成為桌上的照片。讓他們成為信託帳戶上的名字。讓他們隨水流逝。明白這個道理,並沒有讓我更容易鬆手放他隨水流逝。――蒂蒂安,《奇想之年》
如果不是有了小孩,我想我大概讀不懂蒂蒂安的《奇想之年》。
事實上,我可能會因為筆觸關係,把這書讀成一本女性版的冷硬派推理小說。
我會把蒂蒂安想成是女的「史卡德」,失魂落魄地四處行走,用著幾乎沒有形容詞的文字冷如刀割地描述一切,偶爾冒出一兩句直如烈酒的句子,讓讀者也跟著醉了起來。
史卡德,卜洛克筆下的紐約私家偵探。他本來有個自己以為美滿的家庭――一個太太和兩個小男孩,也有個自己以為堪稱正派的職業――警察,然而,當他某次執勤誤殺了位無辜小女孩後,這一切都變了,他所以為的正義不再是正義,他所認定的美好生活,開始留下陰影,世界不再那樣非黑即白,有許多的無解、有許多的無奈,而答案卻總是海市蜃樓,想抓也抓不住;人們在無解無奈之中,只好掙扎著尋求慰藉、快樂,及時行樂才是王道。
他,一個中產階級,如今開始流連在酒吧間,也辭去警察工作,更和家人形同陌路;為了謀生,偶爾在清醒的時候接點私人委託,賺點外快,一個闌珊身影徘迴於紐約街頭,四處打聽消息,和許多從不曾出現在中產階級生活裡的人物打交道,趁酒癮未發之前把錢賺到手。看史卡德辦案,究竟破案了沒並不重要,儘管每次他的破案都那麼精彩,在亂如麻的線索中,硬是能抽出條接近真相的繩頭;真正重要是他紐約的踽踽獨行,以及沿路上認識到各種身懷絕技的牛鬼蛇神,我們從他的眼中,看見了一個被股票指數、經濟成長率、資本主義所拋棄的世界,以及在其中努力生活著的形色人物。
蒂蒂安,文藝界享有盛名的女作家。本來也是有個堪稱完美的家庭,同樣是作家的先生約翰,風趣幽默,而所領養的女兒琪恩達娜,溫柔體貼,幾個月前才剛在教堂裡結婚,正幸福美滿。突然間,琪恩達娜因不明原因在聖誕節前幾天陷入昏迷,正為女兒病情擔憂不已的蒂蒂安,又一下子遭逢丈夫約翰心臟病發,眼睜睜地看著他死在眼前。一夕間,天地倒轉,蒂蒂安卻仍得硬吞下丈夫過世的痛苦,撐著身體隨侍在病情仍舊不穩的女兒身旁。
死亡像把利刃,無情地在蒂蒂安現在和過去的生活中間,劃上一道永遠無法還原的鴻溝,如今的她在這一頭,逝去的先生和醒來後又昏迷的女兒在那一頭,只能藉著回憶去追尋,而每次追尋又只是徒增心中的悲痛。於是,蒂蒂安帶著同樣闌珊的身影,徘徊在家與女兒住的醫院之間,徘迴在工作和如今只剩一人的房子間;她接的案子是查明丈夫心臟病發時,究竟是死在自家客廳、救護車上,還是在醫院的急診室裡,然而,所有讀者都知道,這個案子到最後就算水落石出了也不重要,而是蒂蒂安那雙悲痛的眼、那支顫抖的筆,一次一次帶領我們進入喪失親人後的世界,去品嚐健康安樂生活永遠不會察覺到的各樣滋味。
是因為有了小孩,我才知道該怎麼去讀蒂蒂安的某些篇章,但也不是全部。這些篇章特別集中在和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兩件物品上:電話和網路。
我記得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小孩得了腸病毒,是某天中午吃飯時,正和同事聊得起勁兒,突然接到電話,老婆告訴我,保母帶心華去看醫生,懷疑才一歲多一點的心華得了腸病毒。我是一個新手爸爸,卻也知道腸病毒是近年來幾種致孩童於死的嚴重疾病之一,那一剎那間,原本的聊興全部不見,只覺全身上下被一桶冰水淋過,身邊的一切事物,不管是摸的、看的、聽的,全都變得非常不真實,我像個遊魂,在辦公室裡捱著過完下午。
那之後的幾天,只要是在辦公室,我都非常害怕手機或者電話響起,賞心悅耳的鈴聲,聽起來都像半夜偶爾驚醒,那高八度呼嘯而過的救護、救火車聲音。一顆心七上八下的,就擔心打電話來的是保母或太太,她們要告訴我不好的消息。
在《奇想之年》裡,不知是否我自己神經有問題,總覺得「電話」這礙眼的東西,也三不五時經常出現。當先生心臟病發時,蒂蒂安就得在最短的時間內,撥打她抄在「電話」旁邊,「本來是為了萬一大樓裡有人需要救護車」而寫下的醫院電話;當醫院方面告知她先生子已然過世後,蒂蒂安又得面對「電話」了,她必須在幾乎麻木的狀態下,打「電話」給她先生的哥哥,告訴他這件她自己根本就嚥不下的消息;「電話」還沒完呢!隔天一大早,鈴響,電話那一頭問:「願不願意捐贈丈夫的器官」,然後「千頭萬緒湧過我心頭,第一個閃過我心裡的字是『不』。」;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女兒從昏迷中中轉醒,也帶著大病初癒的身體出席了父親約翰的喪禮,然後乘著飛機回到住的家裡,蒂蒂安本來以為,自己可以好好專心面對哀慟了,就在此時,電話又響了,那個老早應該順利搭完飛機,回到家裡安心休息的女兒,卻又因昏眩跌倒、顱內出血,進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中心,進行緊急的神經外科手術……。
心華生病的那幾天,只要我一有空,就會情不自禁上了網路,像發了瘋一樣,四處搜尋和腸病毒有關的資訊;管他是那家醫院的大牌醫師,或只是某個不知名的網路消息來源,我都一字不漏地詳細讀完,儘管我告訴自己,這是為了能夠在接下來心華的病程中,更知道自己該做些什麼。事實上,在我心的最深處,我想找的是一個答案,我希望從網路上找的既不是資訊,不是照顧原則,我希望找的是一句話,那句話說,心華能夠捱過這一回。
我發現,蒂蒂安也是這樣。她瘋狂地上網,一方面找尋和她先生心臟病有關的訊息,究竟是哪個環節導致他血管阻塞、什麼時候他失去呼吸功能,另一方面則是有關她女兒顱內出血的照顧法則。說她是為了更了解丈夫的死因也好,是為了知道女兒當前的狀況也好,事實上,她在尋找的,一樣是個她想要的答案――她先生並沒有真的死了、女兒也將會健康地活下來。
雖然讀進了蒂蒂安寫的某些篇章,然而我必須老實承認,還有許許多多的篇章,我是看不懂的。我不想為賦新辭強說愁,當蒂蒂安用了那麼多篇幅,在追念她先生,在處理自己的哀痛,我是真的有些讀不進去,特別裡面出現的幾次「沒人眷顧麻雀」,隱隱然在質疑著聖經裡的篇章:「若是你們的父不許,一個麻雀也不能掉在地上。」
當然,我還是把這些部分讀完了。我不會針對這個部份多說些什麼,也不願意針對蒂蒂安的文字給予什麼批判,畢竟,我自己尚未走過這樣的悲痛,尚未經歷過身邊最親的人離我而去的黑洞;我沒有資格。
不過或許是蒂蒂安的緣故吧!!我把盧雲的《念――別了母親後》、伍斯特福的《愛兒輓歌》、魯益師的《卿卿如晤》翻了出來,希望這些書能夠幫助我,當靈魂的黑夜來臨,我還有那樣的力量和眼光,看見上帝手中捧著的麻雀。
其實,每每在常見的、尋常的、平凡的事件中,人會碰觸到人生的奧祕。在小孩誕生、異性相擁、父母去世的時刻,生命的奧祕會向我們顯明,正是當我們最富人性情感、最深入接觸到把我們連繫起來的東西時,就會發現生命隱祕的深處。――盧雲,《念――別了母親後》
本文出自「阿祥與dannyboy的對談--閱讀手扎」部落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