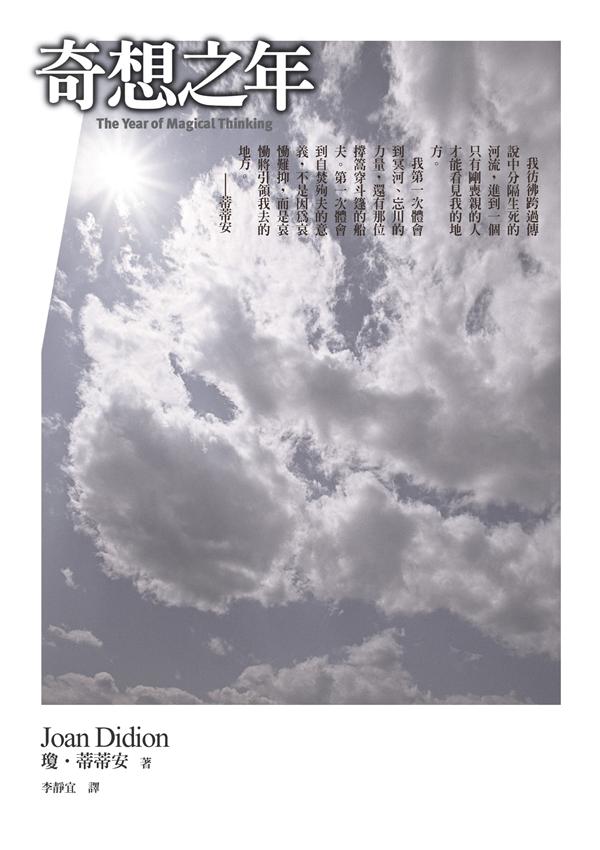
「[創傷]總是一個傷口哭喊的故事,試著告訴我們一種別無他法呈現的真實。這種真實──總是遲緩出現,延誤訴說──不只連結已知,而且聯繫著我們行事言語中的未知部份……」 克魯斯 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4).
2003/7/26:蒂蒂安女兒琪恩達娜的婚禮
2003/12/25:琪恩達娜感冒轉肺炎再轉敗血性休
克,因而住院
2003/12/30:丈夫約翰在飯桌前死於冠狀動脈疾
病
1~3天之內:蒂蒂安寫下「人生變化如此之快/
轉瞬之間人事全非……」幾行
2004/1/22:琪恩達娜出院,由蒂蒂安照顧
2004/3/23:俟琪恩達娜可以行動,約翰的告別
式方始舉行
2004/3/25:琪恩達娜因腦出血又住院
2004/4/30:琪恩達娜與蒂蒂安由加州返回紐約,琪恩達娜在魯斯克中心接受治療,開始逐漸
恢復,蒂蒂安則開始整理房子
2004/5/12晚11:11:蒂蒂安把檔案打開再儲存,未加任何字
2004/10/4:蒂蒂安開始寫作
2004/12/31:《奇想之年》寫作完畢
2005/8/26: 琪恩達娜過世
2005/10:《奇想之年》出版
2007 春:蒂蒂安改編的《奇想之年》戲劇在百老匯上演;《奇想之年》中文版在台灣出版
將這些日期以順時序、直線式排列一方面顯示在短短三年半的時間內瓊.蒂蒂安的生命產生了多麼劇烈的轉變。另一方面,這條單一的時間線卻好像呈現一個「創傷-克服創傷」的快速發展,而掩蓋了在喪親者心中反覆縈繞的哀慟、追悼與思索。
同樣地,表面上蒂蒂安冷靜地面對約翰的死亡,處理他的遺物,讓一旁協助的社工人員稱:「她是很冷靜的當事人」。但實際上我們要問的是, 面對結縭四十年丈夫的突然死亡以及女兒的重病,蒂蒂安如何冷靜?她的思考為何奇異(Magical)?身為小說作家的她為何選擇寫回憶錄,記載一年的零碎思考,而不寫小說或悼亡輓歌?冷靜的敘述是創傷的反覆演出,還是逐漸解決?
我認為蒂蒂安的冷靜是一道心理防線,避免被縈繞於心的回憶瓦解,被哀慟的漩渦淹沒。蒂蒂安的「奇想」不是奇幻之想,而是非理性的冀求丈夫歸來,女兒康復,反覆地回顧過往細節,不斷「閱讀,學習,蒐集資料,埋首文學」(32)。在《奇想之年》中,我們閱讀到的既不是寫實重現或重演(acting out) 創傷經驗,也不是女兒康復、傷痛者痊癒的快樂結局;而是蒂蒂安藉由奇想、回憶細節與研究文獻讓創傷傷口哭喊出來,藉由問問題和尋找線索獲得主觀的答案、非理性了解。一年的經歷所記載的是不斷解決(work through)創傷的過程而非結果。
哀慟的書寫與軌跡
蒂蒂安的冷靜既是她的特色,也是不得已的「表面」反應。她小說文體的特色就是以冷靜的口吻,具體、簡潔卻不連貫的敘述,呈現美國家庭的破碎和價值的喪失。但是這種冷靜卻蘊藏著無以言喻的感情(或用沙則賴Szalai的話,結合了「距離和情感」”remove and emotion”)。在丈夫約翰過世之後,她專注於冷靜行事,實際上也是一種受創傷者的保護裝置。
佛洛伊德指出創傷的過量刺激,往往超過精神裝置的容忍度,無法循「恆常原則」(principle of constancy)加以發洩(abreact)與「卸載」(discharge)刺激與刺激引發的強烈情感(張)。在這種情況之下,人的反應往往是破碎的:感官與理性分離,或專注於某種感官反應。所以,如果一些受創者當下會失去理智、歇斯底里,蒂蒂安的反應則是另一個極端:她「關閉了所有反應」(14), 冷靜地完成「非做不可」的事(21),「……全辦妥了……承認他已經死了。[她]用[她]所能想得出最公開的方式把全辦妥了」(31)。
蒂蒂安專注於思考,可是她的思考並不一致、理性──反是奇異的。這種非理性的思考最錐心刺骨,令人感同身受。縈繞在蒂蒂安心中,最常見的想法是:約翰還可以回來的!因此,她收拾約翰的遺物時,心裡想的是:「他會知道我能打理事情」(14)。她「非做不可」的事除了告知親友外,還包括她必須要獨自一人,「這樣他才能回來」(24)。她利用儀式宣告約翰死亡,但思緒「仍然莫名所以地飄忽不定」(31);她行之如儀,卻嘆道「還是沒能把他帶回來」(32)。
蒂蒂安的哀慟書寫的特色就是它夾雜著非理性的奇想、破碎的回憶,和近距離的理性分析。在哀慟中,蒂蒂安了解失去年邁的父母和喪夫不一樣。年邁的父母過世使她感到「悲傷、孤獨…懊惱」。但失去約翰的哀慟就不同了:「哀慟沒有距離」。她用暗喻和具體的身體感覺來描述它:「哀慟會一波波襲來,突然發作,頓時驚懼憂心,讓人膝蓋發軟,眼睛發黑,…」同時她引用一位精神科主任的研究報告,更進一步呈現「肉體的痛苦感覺會一波波出現…」(20-21)。於是,這種簡短內斂又達及體膚(fully embodied)的語言點出了蒂蒂安的哀慟,不自憐/戀地引起讀者共鳴。
理性分析可以引發感情共鳴,具體的意象可勾勒出到達哀慟深淵的路線,但哀慟的深淵仍是不可探的。觸景可以傷情,為了避免她所謂的「漩渦效應」,蒂蒂安解釋她如何規劃每天的「路線」,安排每天和兄嫂吃飯,避開會聯想起約翰和琪恩達娜的地方。但是陷阱無所不在。一個廣告熟悉的海岸公路畫面可以讓她回想起琪恩達那出生後三天他們一家人回家的景象。在琪恩達娜的醫院裡,她眺望著解凍的河流,想著自己的小說《盡其在我》,以為可以因此不要思考女兒的病況。但是她在回憶中繼續「前行」,就知道「自己已踏進了更加危險的水域」,想到琪恩達娜三歲的情景與約翰對她的忠告。整段漩渦經驗以「知道這個特別的漩渦是怎麼吞噬我的了吧」結尾,但所呈現的仍是看似客觀、不摻雜感情的生活細節和隻字片語(77-78),留待讀者去想像、感受被哀慟吞噬、掉入深淵的經驗。
自覺自問,建構意義
不僅是哀慟的情感無法完全呈現,創傷的經驗亦然。受創的當下是一片渾噩,之後更有許多問題和細節「遲緩出現,延誤訴說」,在受創者心中縈迴。蒂蒂安的敘述反覆執著於一些令她悲痛的細節和問題,但是它們同時在她的奇想、閱讀和敘述中產生意義,助她走過並再現創傷。
蒂蒂安的執著反覆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不是重複強迫(repetition compulsion), 而是在重複中推演意義。蒂蒂安有太多大大小小的問題和遺憾;小者如:救護車在她打電話後到底多久抵達,在急診室等待時,是她冷還是房間冷,急救時約翰跳一下是心跳還是電力使然,是誰清除了約翰的瘀傷。大的問題則包括:約翰可否救活,死者可否回來,為何簡單的感冒會轉為敗血症,她為何不早聽約翰的建議生活放輕鬆些……等等。
執著中蒂蒂安也反覆想到許多蘊含著感情傷痛的細節和隻字片語。約翰的血跡、門牙、瘀傷、眼睛,鞋子都是她在第一、二章所不能釋懷的細節。但全書中反覆出現的字句則更深刻地顯示她對丈夫和女兒的愛與面對死亡的悲哀。第一章約翰過世的那晚,她指出他們是生了火要在家裡吃晚餐。第五章火的意象由約翰死亡轉到五天前夫婦聖誕節時對女兒的感覺:「[他]們生了火。她會很安全」。安全的含意則在第九章蒂蒂安在醫院照顧時變成母親對女兒的承諾:「你很安全,我在這裡」。直到二十一章,女兒要出院時,「你安全了,我在這裡」是母親的信念,雖然她知道「碎碎人」(死神)無所不在。約翰在離開醫院前對女兒說他愛她「比再多一天更多」更產生了深刻的意義,因為它後來不只成了母女倆人對約翰表達愛的方式,也暗示至親至愛的感情可以勝於所能數算的日子。
除了奇想和反覆思索外,身為一個作家,蒂蒂安走過(work through)自己創傷的方式還包括把傷痛、奇想和思索的經驗付諸文字,並很自覺地賦予它們解答、意義和形式。面對人生創傷,我們必須要接受的是並非任何事情都有正確答案的,但是受創者還是可以走過並了解(work through)自己的創傷,找到自己的(主觀的或非理性的)答案。
一方面,蒂蒂安並不耽溺於個人遭遇的哀慟細節和無解之題,她由文學、新聞事件中求得共鳴,由心理學理論中尋找解答,更由醫學文獻中試著尋覓治療女兒病症的方法。另一方面,她試圖了解意外的來龍去脈,回溯約翰過去的隻字片語以找出他身亡的線索。她發現了明確徵兆如1987年他的心臟病就被稱為「寡婦製造症」,以及2003年11月約翰堅持要去巴黎,擔心以後不能再去。
其他一些徵兆──如留言機的留言是他的聲音,他願意和蒂蒂安分享他的筆記,以及25年前他對蒂蒂安寫作的肯定──則好似顯示美好人生必然無常。最客觀的答案應該是蒂蒂安一年後收到的驗屍報告。她反覆閱讀,理性的心靈完全了解,非理性的部份卻仍然不能接受。於是,她把「劇情」再度拉回1987年約翰第一次患病和動手術之時,同時用「再多一天,我愛你比再多一天更多」表達遺憾和延長時間的企圖(141-42)。
寫作的過程也是尋找、產生意義的過程。在蒂蒂安筆下,生活細節如火和照片有了象徵的意義:寫作中她「發現」自己很強調火,因為火代表他們在家。哀慟之初,她避開不看家人的照片,但對它們暸若指掌。完成回憶錄之際,她「知道」她應該讓死者「成為桌上的照片;…他們隨水流逝」(155)。
此外,文本還有許多經由形式對比產生的意義。比如:蒂蒂安最早寫下的兩段話(有關人生多變和她的自憐,改變發生在平凡無奇的一瞬間)是本書的兩個中心思想。第一章點出約翰的死和許多意外一樣是在平凡無奇之中發生的悲劇;第五章她開始討論琪恩達娜的病,又由約翰的死開始講起,然後談到琪恩達娜的流行性感冒是另一個「平凡無奇」;第八章,在另一個平凡無奇的一瞬間,琪恩達娜在加州機場昏倒。「自憐」的意義也在文本中發展:它出現在蒂蒂所寫的第一個段落中。
第六章她是自責的:自憐意味著她把約翰死亡之事當成是發生在她身上的事(54),同時責怪自己對約翰相信自己將死的想法「置若罔聞」。十七章她接受自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情愫,過度自責反而會耽溺於其中。(當然,此議題的延伸在本書的書評中出現。)
蒂蒂安以具體、近距離、反覆的方式書寫創傷細節,以產生形式和建構主觀意義,但是《奇想之年》不但意義不斷發展,它的形式和結尾也都是開放式的,供讀者多元詮釋。同時身為一個記者和小說家,蒂蒂安屢次質疑小說敘事的權威。
在小說《民主》她是一個記者角色,也表達反對小說家的權威。在《白色相簿》散文集(The White Album)中她則表示她所報導悲劇讓她懷疑自己「利用敘述情節線加諸散亂圖象」 的能力。《奇想之年》的蒂蒂安更不是一位敘事權威,而是一位走過創傷的意義建構者。雖然本書有許多反覆的回憶片段,它的章節安排是有秩序的:由約翰死亡開始,談他的後事,然後處理女兒的病與照顧她的經過。在女兒情況好轉時,再回轉呈現對約翰的哀悼。
和本文首的時間表不同的是,《奇想之年》既沒有呈現第二個悲劇的結尾(女兒死亡),也沒有顯示蒂蒂安對約翰之死完全釋懷。一年畢竟是太短的療傷時間,現實的發展也必然在敘事控制之外。蒂蒂安可以建立許多意義;在理性地層面她了解約翰的死因,接受他的死亡。但是本書結尾她所呈現的仍是約翰的建議,約翰「確實」這樣告訴她。至於蒂蒂安為何不在出書之前加一個女兒過世的註記?書評者各說紛紜,我則認為那個註記會打破本書形式的完整,以及減低現實的紛亂。
畢竟,蒂蒂安再現自己走過創傷的過程之初,她已經預料到讀者會有不同的詮釋:她「讓[我]們揀選段落,以各自不同的詮釋手法,用迥然相異的方式唸出相同的台詞。」這個創傷再現的故事還未結束,07年春天本書的戲劇版才要在百老匯上演──或者說類似的劇情一直在人類舞台演出著。
引用書目
Szalai, Jennifer. “The still point of the turning world: Joan Didion and the opposite of meaning.” (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Book Review) Harper's Magazine, Nov 2005 v311 i1866 p97(5),
張小虹.〈看‧不見九二一:災難、創傷與視覺消費〉 《中外文學》30.8(2002-01): 83-131.
(本文作者為輔大英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