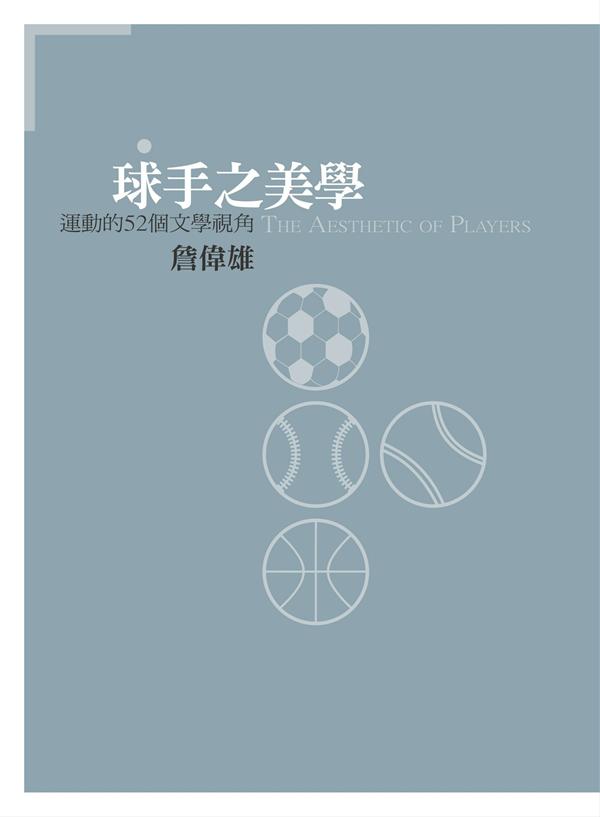
每個人都或多或少曾經有過球類運動的經驗,在台灣而言,就是棒球。這種運動與其說它考驗體能,不如說它考驗人的穩定性、應變能力、精準度、判斷力、以及謀略。棒球打得好的人,必得要有天份,也要有苦練,還要學習判斷對手的球路、心情、喜好。
不聰明不沉著的人是打不好棒球的。
籃球、足球、網球和高爾夫球,也是如此。一個人的運動講的是上天給的天賦和苦練的意志,團隊的運動還得要加入默契和協調能力。
詹偉雄是個極其聰明的人,第一次見到他,印象就非常深刻。那一次見面是開會馬拉松,我們從黃昏六點馬不停蹄開會開到半夜十二點,開足了六小時,但是大家竟然一點也不感到疲憊,也絲毫不感覺時間飛逝。他腦子非常快,又不至於快得把人拋在後面﹔他的狀態很沉穩,又不會穩得把人悶死﹔他旁徵博引,又沒有絲毫炫燿的意味。一個在職場上這麼成功的人竟然沒有一點虛浮,這麼聰明的人竟然沒有一點驕氣,簡簡單單穿一件T恤,自然捲的長髮綁在腦後,笑起來很溫暖,很踏實。原來社會上真的有這樣的人存在。
這樣的人會喜歡球類運動,完全在預料之內,他會從各種文學、繪畫、音樂、電影、戲劇等藝術形式來寫球類運動,也在預期之內,但是,你絕對料不到他寫得如此變幻莫測。從川端康成、馬奎斯、普魯斯特、波赫士、哈威爾、卡夫卡、福克納、常玉、黑格爾、馬克思、韋伯、Bob Dylan,一直到波特萊爾、達文西、蘇格拉底、莫扎特、荷馬的史詩、蒙德里安的畫作、Queen合唱團等等,不可勝數,每一篇都有一個美學主題支撐他的球論。所以,當「打擊的辯證」或「一個幽靈,一個足球的幽靈,正在歐洲的上空遊蕩」或是「球打得像莫扎特的小夜曲」這樣的句子出現時,作者那熱情又浪漫的球類美學,簡直像是球手內心裡澎湃的靈魂,勢不可遏,迷魅了每一個觀者的眼睛和心靈。
什麼樣的人打什麼樣的球,如果詹偉雄是個球手,棒球而言,他是擅長飄忽變化球的投手﹔籃球而言,他是謀略大膽的教練﹔足球而言,他是主控全場的中鋒﹔網球而言,他的底線抽球和網前截擊一樣有力﹔高爾夫球而言,嗯,說實話,他太揮灑了,看起來不像是會打這種球的人。
不過,不管是哪一種球,他一定是勝利之後會跪下來親吻草地的那種人。
我覺得他最像個投手,面對他,你會突然發現你自己是個打擊者,你面前這個笑嘻嘻的投手擅長打心理戰,哪個角度的變化球他都有辦法操控,再無關的美學主題都能突然成為球類運動的相關思考,而且他穩控全場,你必須有對等的美學訓練,如此他的每一球你都能接,你的每一招都不虛發。你會一邊接他的球,一邊在心裡笑,嘖嘖,這傢伙,好樣的。一種棋逢敵手的快樂。
詹偉雄寫出運動的另一種意義:不論輸贏,能和聰明的人交手,真是太有意思太愉快了。
(作者簡介:柯裕棻,作家,喜愛觀看各種運動轉播,甚至於幾度荒廢學業,現任政治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